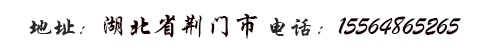管理理论分析团队路线的人事逻辑
|
白癜风是什么引起 http://pf.39.net/bdfyy/bdfjc/180910/6515551.html 当年在知乎有一个问题,什么是你当领导以后才知道的? 我的回答是,最重要的是资源,最关键的是选择,最困难的是组织。一群没有挑过大梁的喷子,以为当领导就是办公室宫斗,看到这样的回答,叽叽喳喳,纷纷反对。夏虫无法语冰。 现在想一想,最重要的是资源,最关键的是组织,最困难的是选择,似乎更合适。 没有物质资源,任何意志也贯彻不下去,团队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每一个团队,往往在成立之初,就打下了发展路径的烙印;对未来的判断,如同在迷雾中开车,更多的是经验和直觉。 关于物质资源的重要性,在《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等文章之中,已经多次分析,而且还将不断分析。这次分析一下团队组织与团队政策选择的相互关系。 《三体》之中的黑暗丛林法则很短: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双方无法判断对方是否为善意文明,文明之间优先选择打击。 《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的核心观点也很简单:任何政治运动都必须有对应的物质基础,都必然向增加物质资源的方向发展。 政治理论分析: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 这篇文章可以算作《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的姊妹篇,核心观点也很短:特定的路线产生特定的利益。特定的利益产生特定的人群,特定人群强化特定的利益。这是一个互相强化、因果互动的过程。 通俗点说,就十个字:路线决定人,人决定路线。 随便举个例子: 许多谈论二战战史的人,喜欢批评日本联合舰队虽然在偷袭珍珠港之中取得重大战果,却仍然热衷于“大舰巨炮”主义,总是试图追求战列舰决战。 是日本人脑筋僵化,冥顽不灵吗? 事情显然不这么简单。 日本联合舰队一战成名是在对马海战之中,联合舰队使用T字阵头战法,全歼长途奔袭的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 日后二战期间的日本联合舰队高级将领们,此时或者在舰队之中对俄作战(山本五十六),或者刚刚进入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南云忠一),或者即将进入江田岛海军兵学校。 年12月,莱特兄弟试飞飞机。早期飞机性能低下。年,日德兰大海战,决战双方仍然以战列舰决胜负。 对日本的海军将领们来说,飞机显然不是他们接受海军教育时代的主流兵器,他们也很难有舰载机飞行员的经历,他们擅长的是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战术,而不是指挥舰载机远距离搜索歼敌于战列舰火炮射程之外。 除了个别人外,绝大多数人已经看到了舰载机已经取代了战列舰的炮弹成为距离更远杀伤力更大的打击手段,但是却不愿意让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成为特混舰队的核心。 即使山本那样在美国担任过武官的将领,视野开阔,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也仅仅把舰载机攻击作为削弱对方舰队作战的重要手段,而不是决胜手段。舰载机攻击,是为下一步战列舰对决创造有利条件,而不是直接歼灭对方舰队。 如果舰载机成为核心打击力量,那么舰队司令必然由航母舰长出身,航空母舰舰长最好的人选无疑是有航空兵经验舰载机飞行员。 如果按照这样的路径晋升,在无形之中就切断了很多接受传统“大舰巨炮”主义教育日本海军军官的晋升之路。这样的路线转型,显然会受到巨大的阻力。 如果按照这种发展路径,南云忠一所擅长的使用舰炮、鱼雷,组成T字阵型在视野内对决的作战技能将大大贬值。他除非人到中年重新改行,接受飞行员培训,从头再来,从零开始,否则无缘舰队司令。现实之中,南云忠一一旦改行,必将将无缘舰队司令——因为即使他肯从头开始,也显然很难从数量众多的年轻晚辈中脱颖而出。他是否会全面接受一种让自己拥有的所有资源全部归零,自己从舰队司令跌落到初出茅庐的准尉的理论?这是不言而喻的。 反过来,如果坚守“大舰巨炮”主义,那么大批南云忠一的下属将按照南云的发展路径,在南云等前辈的选择提携下,一步步接过南云等前辈的衣钵,走上舰队司令的岗位。以南云的经验和经历,他是会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提拔自己熟悉的下属,还是会在自己陌生的领域提拔自己陌生的飞行员?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相比之下,山本有担任航空队副队长的履历和学习驾驶的经历,拥有驾驶飞机的经验和航空后备干部的人选,缺乏舰长到舰队司令的成长历程。所以,他乐于鼓吹航空力量大规模扩张航空母舰。航空兵力量的扩张,显然有利他的晋升。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过中年,他的飞行技能和飞行经验和晚辈年轻人相比,只能算平平,他必须依靠海军的传统才有资格成为新兴的海军航空兵的司令。 作为过渡人物,山本在海军高级军官中飞行经验最丰富,飞行员中资历最老。所以,他的路径必然是一面大力鼓吹航空兵,一面又不能彻底放弃“大舰巨炮”主义,搞田忌赛马。 何况,即使山本主动放弃现有的“大舰巨炮”主义,全力支持“舰载机决胜”主义,把自己的位置让给航空兵出身的后进晚辈。这些晚辈显然也不是南云忠一等舰长、舰队司令出身的传统势力的对手。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去山本羽翼呵护的航空兵晚辈军官们被边缘化。 传统海军军官擅长的使用舰炮、鱼雷、T字阵型在视野内对决的作战技能,决定了联合舰队的“”大舰巨炮“主义”的作战思想。联合舰队的“大舰巨炮”主义的作战思想,又给擅长舰炮、鱼雷、T字阵型在视野内对决的作战技能的海军军官更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虽然联合舰队的大多数高级军官都已经认识到了飞机航程远,机动性强,攻击准确等优点,一部分人甚至乐于组建庞大的航空母舰和舰载机部队,却仍不愿意让“舰载机决胜”主义取代“大舰巨炮”主义——航空母舰是战列舰有益的助手,可以有效削弱甚至歼灭对方舰队,要多多益善,却不能是海战的核心兵器。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发现新的发展方向不难,主动支持新的发展路线,自己放弃现有的地位和资源从头再来,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魄很难。何况,即使个别人有这样的气魄,他们也会很快被团队其他绝大多数恋栈的同僚边缘化。 与日本联合舰队航空兵部队类似,二战以前,装甲兵部队在许多国家传统陆军中的地位也不高。 传统陆军讲究阵地战。坦克是攻坚的武器,是防守利器,是步兵的得力助手,为步兵突破铁丝网、机枪阵地服务。汽车则是运输重炮和补给弹药的重要交通工具。虽然装备了大量的坦克,但是大多被拆散到步兵部队中,辅助步兵进攻或防御,用于短促突击和反冲击,难以形成快速远距离突击的核心力量。 以德国为首的机械化军团则讲究威力和速度。坦克集中使用,形成突击力量,迅速突破对方防线后,向对方纵深发展,如入无人之境,占领交通枢纽,切断对方的后勤补给,摧毁指挥中心,粉碎对方的有组织抵抗。对方很快就会被分割包围,陷入各自为战、弹尽粮绝的绝境。步兵为坦克服务,全部上车跟上坦克的进攻速度。汽车源源不断地为高速冲击的坦克军团运输步兵、重炮、燃料、弹药和零配件。 两种战法,孰优孰劣,高下立判。一旦德军的坦克突破了对方的防御阵地,对方行动迟缓的步兵和分散的坦克,将毫无还手之力。 盟军方面,并不缺少认识到坦克对战争作战方式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军官,比如写出《装甲战》的英国富勒,比如写出《建立职业军》的法国戴高乐。 但是,这两位都受到了强烈的打压,装甲战取代阵地战,那些传统军人干什么去?退役还是从头再来? 如果英国和法国的陆军转向使用富勒和戴高乐的理论,装甲师成为军队核心,那么装甲营扩张为装甲团,装甲团扩张为装甲师,装甲兵们士兵变班长,班长变排长,排长变连长,连长变营长……与之对应的必然是传统军人之中从步兵出身的军官难以晋升,只能原地踏步,甚至提前退役。 富勒和戴高乐的理论,不遭受强大的阻力就奇怪了。 此外,抛开前面的提到的原因不谈,戴高乐受到打压的原因,至少还涉及修建马其诺防线巨额的利润——装甲战取代阵地战,与传统军人关系密切,擅长修建钢筋混凝土工事的军事承包商的利润岂不全部成为泡影? 可以说,相比保守的英法陆军,日本的海军还是比较开明的。 贯彻任何意志,都要提供对应的人、财、物等资源,具体说来,包括权力、金钱和晋升空间。这些资源必然产生对应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必然尽量争取更多的资源,巩固并扩张现有的资源。争取更多资源,巩固并扩张现有资源的最有效的方式,自然是推进现有的路线。 这就是路线决定人,人决定路线。 路线必然产生对应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必然强化路线。团队新成员的发展,必然依赖老前辈的推荐和提携。老前辈会选择什么样的人?任何试图改变路线的行为,都必然冲击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地位,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使用现有的一切资源全力对抗。 要改变路线,必须淘汰原有的利益集团。 这就是常说的,一群人上,一群人下。 以联合舰队的航空兵、富勒准将和戴高乐上校的地位和拥有的资源,显然无法抗衡原有的保守势力。虽然舰载机和坦克军团致胜的迹象已经极其明显,但是联合舰队和英法陆军,都不会主动接受未来的趋势。 《三体》小说之中,人类受到三体人威胁后,决定建造恒星际战舰。恒星战舰的发动机有两种研究倾向,即有工质发动机和无工质发动机,有工质发动机与传统化学火箭发动机接近,潜力有限,无工质发动机脱离与传动化学发动机的联系,潜力更大。老一辈航天要员均是研究传统化学火箭发动机出身,他们的经验局限于化学火箭发动机,他们的选择是什么,不言而喻。 这种情况下,为了全人类的未来,太空军大校章北海,狙击了老一辈航天要员,并把暗杀行为掩盖成流星雨。然后,他进入冬眠状态。几个世纪以后,他醒来的时候,人类太空舰队已经成型。恒星战舰装备的全是无工质发动机。 如果没有那几颗子弹,人类太空舰队的发动机大概率是有工质发动机,即使采用无工质发动机也必然是在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以后。 现实之中,即使这几位老一辈航天要员全部被杀,人类的恒星战舰的发动机,估计也是传统保守的有工质发动机。虽然老一辈航天要员死了,他们的弟子会接受他们衣钵,迅速占据他们的位置,继续按照他们思路维护传统保守发动机的发展路径。 除非有强大的外力,否则即使南云忠一中将自尽,自有“大舰巨炮”主义的少将接班,轮不到海军航空兵出身的平田一郎少佐越级晋升接班。 那么,为什么德军可以顺利发展新型战法呢? 年的长刀之夜,希特勒处决了试图垄断暴力的罗姆等人,获得了国防军的支持。 年,希特勒对国防军出手了。希姆莱先是举报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的夫人曾经是妓女,希特勒直接将布隆贝格撤职,并将其从军团将领中除名。代表国防军保守势力的弗里奇成为最有可能接替布隆贝格的成为国防部长的人选。于是,希姆莱又诬告弗里奇犯同性恋罪,希特勒趁势解除了弗里奇的职务。 希特勒一面打压传统势力,一面提拔重用军官团中的少壮派。古德里安、隆美尔、曼施坦因等人脱颖而出。这些接受坦克战思想的军官被提拔后,自然带动一大批与他们思想接近,有人生交集的下属的晋升,形成新的利益集团。 不换思想就换人,换了人就会换思想。希特勒为了控制德军,打压德军内部的传统势力,在德军大换人,换人的结果之一,是德军换了作战思想。 由于大多数国家都把指挥权和财权赋予不同的人群。所以,希特勒打压国防军军官团只需要考虑到军官个人的人脉和威望,而不用考虑到军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所以,德军的清洗行动相对的容易一些。 如果考虑到物质资源的话。那么这个处理过程就会更加复杂。 一战结束,战后重建中获利的法国建筑商,拥有巨大的财力,自然会搞院外游说,鼓吹战线防御。游说的结果就是法国耗费巨资,修筑马奇诺防线。马其诺防线竣工不久,就被德军突破,法国随即亡国。设想,如果二战晚几年爆发,在马其诺防线上赚了大钱的法国建筑商们会干什么?手里有的是挖掘机,擅长修建铁公基,看什么都想挖两下。他们有挖掘机又有钱,自然不会闲下来。他们会游说议会在法国搞高速公路村村通,还是在法属殖民地继续搞铁公基? 戴高乐不但在职位和人脉上不如传统派,在物质资源上也斗不过建筑商。要取代军内传统派,必须首先摧毁通过修筑防线获利的财大气粗的建筑商。这个任务,显然远远超过戴高乐上校的能量。 所以,摧毁摧毁这种利益集团的事情,只能交给德军去完成了。传统法军被粉碎,建筑商的财产或者被德军没收,或者受到沉重打击。 遵义会议也是如此。如果当时苏联继续大力支援中国革命,那么遵义会议是很难发生的。设想如果以王明为首的留苏派掌握着充足的物质资源,那么他们就有足够的力量阻止本土派的崛起。但是现实之中,“苏联人给国民党金钱、武器和弹药,给共产党送来书本、教条以及留学生”。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留学生们既没有足够的威望,也没有的足够丰富经验的干部储备,更没有按照他们的路线执行,拿得出手的战绩,实现以战养战扩张自己掌握的物质资源、干部队伍和人脉,自然是无力维持其对中国革命的拙劣的控制。于是留学生下台,本土派上台,一群人下,一群人上,中国革命的路线自然从为苏联利益而运动,向维护本土利益而运动了。 与二战类似,如果没有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和对红一方面军的围追堵截,遵义会议也很难发生。蒋介石的围剿和堵截给红军造成重大牺牲和损坏,让红军军心愤懑,摧毁了留苏派的威信,粉碎了他们的统治基础。 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的强力介入,团队很难主动牺牲现有的利益改弦更张。 抛开山本大将、富勒准将、戴高乐上校这些人无力对抗传统军官团,更无力对抗政策背后获益的财阀不说,即使认识到团队路线产生问题的团队领袖,也未必能做到主动改弦更张。 蒋介石不是不知道国民党腐败,效率低下,但是如果他主动改弦更张,更可能的结果不是他清洗国军军官团,而是他被国军军官团所抛弃。触动一个人的利益,会引起一个人的反抗,触动一个团体的利益,会引起整个团体的反抗。蒋介石之所以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领袖,是因为一群新军阀默认没有更合适的人选能替代蒋介石代表自己的利益。如果新军阀们达成共识,认定蒋介石不再是自己利益集团的代理人,而是自己的敌人,那么蒋介石随时失去新军阀的支持。届时,民间穷人支持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新军阀支持新主子为首的国民党,蒋介石在双方都不能获得支持,他只能黯然下野。 即使不考虑下属叛变,蒋介石也可能会发现,自己根本无人可用。汤恩伯贪腐,王耀武忙着做生意,孙元良动辄逃跑,戴笠黑白通吃,白崇禧、马步芳、阎锡山割据一方。把这些人清洗掉以后,蒋介石能启用谁呢?吴敬中站长吗?可能还不如戴笠。启用少校余则成吗?一方面,当时的少校车载斗量,蒋介石可能完全没有接触余则成的机会。另一方面,如何在车载斗量的少校中选拔出具有领导潜力的余则成?何况,即使能选拔出余则成,初出茅庐缺少经验的余则成在短期内的表现,也未必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戴笠。 斯大林为了推进工业化,镇压党内反对派,曾经对苏军大清洗。结果,许多团级甚至营级干部,在短时间内走上师级甚至军级领导岗位。许多人缺乏指挥大军团作战的经验,在德国入侵初期,表现拙劣。新手上路,直接油门踩到底跑高速,自然险象环生,随时翻车。卫国战争后期,这些人成长起来,有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代价则是苏联红军巨大的牺牲。 所以,对蒋介石来说,理性的选择,自然是一面大骂国民党将领腐败,效率低下,一面继续重用这些腐败的将领,一面加紧搜刮聚敛物质资源,一面向美国摇尾乞怜争取物质资源,一面给自己在台湾留退路。 除非以执行某条路线的既得利益为依据,对特定人群进行大规模清洗。否则,违背既得利益的政策是无法推行下去的,而这些特定人群又是现有的统治阶级的骨干和核心人物。这种情况下,特定清洗很可能导致组织的解体。 所以,观察很多路线政策会发现,各国的宏观政策往往是一条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甚至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对普通人来讲,这是路径依赖,但是对于团队来讲,这是有更深层次的利益关系。 对团队来说,没有外来的冲击,不会主动求变。有外来冲击的时候,要么力度不够,不足以摧毁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要么力度太大,把现有的组织一起埋葬。所以,,与日本联合舰队的“大舰巨炮”主义者最终葬身鱼腹,步兵阵地战主义者被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歼灭,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退守台湾一样,许多朝代最后只能被新的力量所替代。 团队内部从领袖到成员,既不能主动改变自己的利益,不能改变路线,也不愿主动退出历史舞台,最终只有被历史前进的车轮碾碎。 某一个团队,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某一条利益路线而存在的,在建立之初,即打上日后发展方向的烙印。 孙中山的团队,大批来自社会中上阶级的留日学生,许多人出身地主和官僚家庭,自然没法完成“平均地权”的诺言。蒋介石的团队,来自更反动的新军阀集团,抛弃了孙中山的梦想,只剩下反动。 一个团队大多数成员的的利益发生变化,团队路线就会发生变化。 在生产力发展受到局限、物质资料还没有极大丰富、不能实现按需分配、私有制将长期存在、个人生活水平还必然出现差距的时代,叛变革命比忠于革命要容易得多。 蒋介石修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叛变革命容易,动员人民打倒新军阀,则绝无可能。他的选择,只能是成为钱最多,枪最多的新军阀,用银弹和炮弹震慑其他军阀。 当然,这并不是说,原有团队的领袖只能束手无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比如生产力发展,从奴隶制进入编户齐民的时代,秦国等国家纷纷采用军功爵制取代血缘贵族制,发动群众斗贵族。 但是,这种成功的例子毕竟是少数,需要有大量的外在前置条件,比如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废井田开阡陌,比如战争的连绵不绝民间战斗英雄脱颖而出,比如民间精英掌握武力可以镇压贵族,比如传统的血缘贵族制让民间精英无法晋升为贵族背叛自己的阶级等等。 由于存在这种人决定路线,路线决定人的人事逻辑,对政权来说,一旦选择了错误的政策,对公司来说,一旦点错了科技树。就麻烦大了。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会轻易改弦更张,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任期制和市场经济淘汰点错科技树的企业的重要作用。 美军出兵阿富汗就形成了特定的利益集团。20年来,美军在阿富汗驻军,美军获得军费、军官获得破格晋升、供应商获得订单。塔利班有空没事给美军打打冷枪,打几发RPG,获得反美势力的资助。双方都有收益。美军甚至可能私下串通塔利班,彼此心照不宣,达成默契:只要你们没事打几枪,我们就有长期驻扎的理由,你们就可以获得其他国家的援助。有些时候,美军指挥官甚至主动把一些士兵送人虎口,让塔利班消灭,换取更多的兵力和拨款。电影《前哨》就是根据这样的真实事件改编。 在阿富汗驻军20年,烧钱2万亿美元,这是多么大的生意?要触动这样的利益集团,只能等新一任总统上台,原有政务官集体辞职。利益集团大规模重新洗牌。 对公司来说,董事会没有任期,但是如果一家企业点错了科技树,就难免被市场淘汰。 不过,并不能对任期制和市场规律寄予太大的希望。美国政府四年一换,可以改变原有政策,比如从阿富汗撤军。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金钱决定谁在华盛顿主持工作的基本规则。同理,如果点错科技树的企业是垄断企业的话,那么被淘汰的概率很低了,往往不是市场淘汰企业,而是企业执意发展方向错误的技术,限制发展方向正确的新技术。至于这家企业一意孤行的代价,自然转嫁给消费者,甚至全民。 按照人决定路线,路线决定的人原则,可以大致预期,各国政治路线的发展方向。 看看有没有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就会知道有没有大规模的路线变动。如果人事没有什么变动,那么政治路线基本也不会有什么变动。而且,这种人事变动应该是以阶级或者财产或特定身份划线,而不是个别人或者小圈子的上上下下生死沉浮。否则,就会导致一个利益集团的前辈倒下,同一个利益集团的晚辈接替,整个利益集团不断膨胀壮大的的情况。这样的团队提出的政策,只能是新瓶装旧酒。 反之,剧烈的人事变动,比如大批商人的子女,迅速占领传统上由知识分子控制的官僚的职位,那么必定推动并将继续推动政治路线的变化。这样的团队提出的政策,必定是旧瓶装新酒。 那么,当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与团队的人事逻辑发生冲突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呢?政治团队解体,政治运动失败。 比如明朝末年,官僚集团的核心来自大地主、大商人阶级。这样的团队,推行的政策必然维护本团队的利益。于是,一面是地主搞土地兼并,一面是商人聚敛金银,一面是加紧增收官逼民反,一面是财政枯竭拖欠军饷。崇祯虽然着急却无可奈何。李自成兵临城下,官僚集团根毛不拔。 崇祯的处境与当年蒋介石相似,要维持明朝的统治,就要推行增加税收,减轻民众负担的政策,却没有可以执行的团队。 以崇祯拥有的明朝官僚团队,推行的政策,只能增加团队成员个人的财富,激化社会矛盾,无法增加明朝的财政收入,使维护明朝统治的政治运动的物质基础枯竭,无力镇压劳动者的反抗。崇祯临死说,“然皆诸臣误朕也”,自然有对自己的骚操作甩锅的成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明朝的灭亡,就是经济逻辑与人事逻辑冲突的结果。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这时,至少会有三种可能:比如,官僚集团内部力量脱离明朝统治,成为军阀,获得独立的经济基础,新生军阀歼灭吞并其他大地主和大商人;比如,农民起义军不断打土豪分田地,壮大财源和队伍;比如,外来的满清统治者入关,跑马圈地,控制经济基础,地方政权升级为全国政权。 这三种可能,都是既符合经济逻辑又符合人事逻辑。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轮回的逻辑。 MRAnderson多谢支持!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asaoa.com/nstq/9003.html
- 上一篇文章: 元色儿童美育馆十月课程主题粉色的巴哈马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