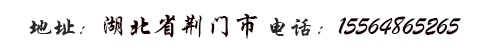美国建筑文化的历史兴衰,19世纪新时代建
|
斑蝥酊斑秃 http://m.39.net/pf/a_4344161.html 引言 建筑师们因地制宜,南部地理环境赋予其新的建筑特征,西部牛仔性格融入其中并折射出鲜活的美国时代精神。芝加哥是美利坚最年轻的城市之一,表面上生机勃勃,铁路运输发达,港口联通四面八方,钢铁厂星罗棋布,其强大的噪音显示出它正准备赶超其他先进城市。 由于年轻的路易斯·沙利文还没拥有对抗复古主义者的力量,虽然他个人设计的运输大楼非常富有特例独行的创造力。可惜鲁特已经离世,他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人,如果他当时活着的话,那么,作为伯纳姆真正亲密无间的战友,他的中正立场应当可以规劝一下伯纳姆的刚愎自用,美国建筑不至于如此误入歧途,病入膏育。伯纳姆具有艺术天赋,但他更擅长权谋之道,把世界博览会与芝加哥撮合在一起,使芝加哥成为这个共和国在建筑方面的第一城市。 也许是为了借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周年之机扬名天下,不可避免地博览会与芝加哥硬生生扯上了关系,同时博览会欲借这个城市表达某些人在建筑领域的强权意识,这个城市则想借博览会给自己装饰一下门面。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博览会在金碧辉煌的后面有许多华而不实的东西,一些糟糕透顶的建筑物被加以批判。亨利·亚当斯对古典建筑的认识水平很高,他指出仿古的巴特农神庙仅仅形似而已,与公元前年建成的原建筑相比之下,一看就是个冒牌货。亚当斯对新时代应该具有的建筑特征也颇有见地,他对博览会做出这样的评论: 对我们这些品质纯真土生土长的人来说,对芝加哥博览会假大空的东西了解多少呢?道德败坏的帽子扣在它的头上也许过分,但虚假成风的恶毒之处在于,它利用了公众不懂得仿古建筑的真谛这一弱点,无法分辨其优劣,我却能为自己不受其迷惑而喜出望外。就像猫头鹰察看一切,我心怀敬重一本正经地瞻仰了所有这些宏大的建筑物,双腿如此疲惫······ 今年夏天,萨金特在伦敦为哈默斯利夫人绘制的肖像,你应该记忆犹新吧?画像似乎表达了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的轻蔑心理,抑或是一种践踏的情绪呢?抑或是对我们的文化恳切真实、栩栩如生地形象刻画······抑或是萨金特已经灰心丧气,向纸醉金迷时代的一位女性低下他那原本高贵的头颅?······嗨,芝加哥博览会貌似壮丽的建筑,多像艺术家笔下那位哈默斯利夫人呀! 与亚当斯惯有的幽默不同,路易斯·沙利文的言论更加富有批判性。他尖刻地说:像小偷一样剽窃历史,花言巧语却显得楚楚动人,引经据典也显得如此高明,但新瓶装旧酒的事干得再好,滑稽戏总有收场的时候,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将看出这一切背后的花招不过是抛弃信仰及道德风尚的堕落。 芝加哥博览会的巨大破坏力会延续半个世纪。因为它弄虚作假之举、背弃道义之风,已经令美利坚的大脑组织产生病变,建筑痴呆症将日趋严重!沙利文的愤激之词当然有些片面,但具有惊人的预见力。在博览会的诱导下,美利坚的古典建筑之花处处开遍,照抄照搬封建主义时代里象征权势的建筑物。 华盛顿的办公大楼采用仿古方式,这样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正向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上飞速前进的民主国家,生气盎然的骨子里,竟然妄想以罗马帝国的外形来包装自己:霍雷肖·格里诺乘机平反,他50年前因为把乔治,华盛顿雕塑成身穿意大利宽袍的形象而获罪;林肯纪念堂也仿造罗马皇帝的模式,而这位伟人生前最反对浮华之风。 从银行到邮局,从车站到私人豪宅,从学校到图书馆,仿古方式只引进不消化,风气在美国弥漫开来。哥特式或罗马式建筑在教堂设计上千篇一律,流风所至,公理教会、唯一神教会曾经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白色尖顶,用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作为他们的样板式建筑。亨特是无数仿造法国古代城堡式私人豪宅的设计者,怀特常常为某些欣赏意大利的宫殿式房屋的富豪服务。19世纪70年代,约翰·菲斯克曾对哈佛大学这样建议:百分之百用牛津大学的哥特式建筑式样来设计建造哈佛纪念堂,而不必采用本地建筑的任何模式。 哈佛大学并不认可他的想法,而芝加哥大学在筹建的时候就决定采用他的建议。无独有偶,普林斯顿大学向芝加哥大学看齐,对拿骚大厅进行改建;耶鲁大学的康涅狄格大厅也遭手术;西点军校因为拉尔夫·亚当斯·克拉姆的倡议修建哥特式建筑;杰斐逊的教诲显然被新杜克大学遗忘了,他们向牛津式建筑看齐;麻省理工学院虽然放弃了牛津式建筑,但他们还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古典式建筑。公众逐渐被这些建筑物搞得麻木不仁,古典建筑设计师们却愈来愈像服食了兴奋剂一般豪情满怀-年,他们在罗马成立了美国学院,以复兴古典建筑学为己任;麦克基姆、米德和怀特公司在古典建筑工程项目上取得垄断地位。 当然,古典派不可能处处都占上风。早在年,一项新的反托拉斯法由美国国会颁布,尽量破除少数大公司的经济垄断地位,参议员约翰·谢尔曼是这一法案的主要发起人。路易斯·沙利文充满质疑的战斗的声音也几乎同时响起: 如今我们正处于美利坚上演一出活生生的戏剧的时候,我们就像钟摆一样,在顽固老朽与开拓创新之间均衡地运动,我们的建筑恰如其分而又实事求是地把这一态势在我们眼前真实呈现出来。顽固派在建筑数量上远远超出创新者,新生力量在这一方面处于劣势是毫无疑问的;创新精神是开拓者唯一的武器,只有积极主动发挥创造力的作用,以高质量的建筑物去抗击老朽们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才有希望打败他们这些顽固派。 然而,现在这仅仅是我的一种推论,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的建筑风格已经糟糕至极、老朽透顶,这一现状必须加以改进。在美利坚的社会生活中,在美利坚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希望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明天终将开花结果,毫无疑问的是,许多新一代有识之士已经认清了这一点。 以上是路易斯·沙利文在《幼儿园絮语》中的一段话。当他名声大振的时候,此书成为了名著。在理查逊和鲁特辞世后,沙利文坚信他自己是属于时代的-只有他预言美国建筑希望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沙利文一向具有惊人的预见力,但他的同时代人一点也不尊重他,大多数批评家都对他冷眼旁观(斯凯勒、斯图尔吉斯等极少数批评家除外),世界博览会之后他几乎找不到设计工作。然而,50年之后他声望愈来愈高,盖过了所有与博览会有关系的其他设计师,成为美国建筑史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人物。 沙利文精通哲理,但他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不强,在演讲时一个简单的问题总是拖泥带水,尤其在非常激动的时候,更是结结巴巴、不知所云;他热爱瓦尔特·惠特曼的诗歌,诗歌是惠特曼宣传民主的载体,沙利文也期望把建筑变成宣传民主的载体。他特别清高,喜欢高高在上的感觉,甚至有虚荣心,但在天生傲骨的背后是个诚实真挚、正气凛然、坦白直率的人。《幼儿园絮语》以及《思想自传》等著述无不带有他诚实真挚、正气凛然、坦白直率的性格特征。 他青年时代就形成了两个基本信念,贯穿着他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一生。他之所以能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是因为心中拥有这两个基本信念:第一个基本信念-建筑功能决定建筑形式,建筑形式只不过是对其功能的表达;第二个基本信念-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果建筑不能实事求是地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那么,建筑就不能产生真正的价值及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这个“建筑功能决定建筑形式”的原则,并非沙利文独创的观念,而是一个始终被大家忽略了的原始观念。 结语 作为美国建筑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沙利文的生涯绝对是特立独行的。他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和美术学院学习,美国第一座真正摩天大楼的建造者詹尼男爵是他的恩师;亨特非常标榜的复兴风格,沙利文颇有涉猎;理查逊钟情一生的罗马式建筑,沙利文也进行过深入研究-芝加哥大会堂就是他所谓罗马式建筑试验的副产品。他是在继杰斐逊之后美国建筑学界的泰山北斗,而且启发了另一位大师级人物弗朗克、洛伊德,赖特的智慧,如今他被誉为“美国现代建筑之父”。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asaoa.com/nstq/10109.html
- 上一篇文章: 张若筠唐艺昕婚礼地点曝光盘点那些热门婚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