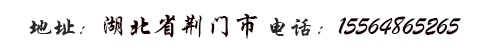博伊斯ldquo纪念碑rdquo
|
前言: 博伊斯青年时学习艺术的方向就是纪念雕塑,年起他在杜塞美院担任的也是纪念雕塑的教授职位。尽管博伊斯积极扩展传统艺术概念,同时使用传统雕塑中不常见的材料,但传统雕塑中长久存在的“纪念碑”主题在他的作品中仍然得到了延续和发扬,其中以《有轨电车站》(Stra?enbahnhaltestelle)和《闪电耀鹿》(BlitzschlagmitLichtscheinaufHirsch)最为突出。 巴洛克遗迹 博伊斯通过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契机实现了一个计划已久的方案——《有轨电车站》。这一作品与博伊斯在克雷武的童年经历有密切联系——埋在地里的铸铁长炮管被四个低矮的迫击炮筒围着,树立在有轨电车站“铁人旁”附近,少年时博伊斯经常在此处等候和上下电车,等车的人们时常坐在迫击炮筒上倚靠着长炮管休息。这个博伊斯仔细端详却依旧感觉费解的神秘纪念碑出自十七世纪爱好建筑和园艺设计的莫里茨亲王之手,时任克雷武行政长官的莫里茨同时修建了多座由战利品组成的纪念碑。这一做法可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经常树立败北敌人的兵器来纪念胜利并彰显自己的强大以避免再次受到战祸侵扰的传统。“铁人旁”站名中的“铁人”原本指另一座位于新动物园圆形剧场的纪念碑,缴获的兵器上安置了身穿铁甲的战神马尔斯雕像。但他在年法兰西革命军进驻克雷武时被损毁,“铁人”这一名称便错误地转给了这些纪念碑中唯一幸存的“丘比特柱”,后来成为“丘比特柱”所在的车站名称。 铜版画《铁人或马尔斯柱》 古罗马银币上树立战利品用以震慑敌人前46-45 年建起的这座巴洛克纪念碑中,长炮管的顶端站立着小爱神丘比特的铜像,一个可爱而充满生命力的孩童形象和下方冰冷且带有锈迹的铁炮形成了强烈对比,意在传达用爱代替死亡,用未来和平克胜昔日战争,这一原始含义也在后来博伊斯的《有轨电车站》中基于第三帝国历史有所继承;地面上以长炮管为中心用碎石组成的八角星指示着八个方向,八个角各放了一枚球形炮弹,呼应了莫里茨亲王的座右铭“向整个地球延伸”。博伊斯日后回忆到,这一纪念碑的局部解剖式呈现深深触动了他,或许也是引导他学习雕塑的起因。 迁至拿骚路旁的“丘比特柱”近影 年底博伊斯和另外两名参展艺术家到威尼斯双年展德国馆实地考察之前,博伊斯曾想在来年的双年展上呈现“蜜泵”(参见“自由国际大学”),但由于泵机的噪音会影响另外两名艺术家的作品,加之博伊斯到访了自己将要使用的展馆中央主室后,决定实现自己长久以来一直构想的“有轨电车站”方案。随后博伊斯获得了来自外交部和联邦土建局的许可——他可以凿穿展厅地板将炮筒和铁轨埋进地里。年4月博伊斯托付从前的学生居斯塔和他的同事进行石膏铸模的翻制工作,翻制的两周间博伊斯也经常到场参与并检查铸模。次月铸造工作完成,铸件红棕色的表面没有打磨加工,而是保持粗糙的质感,铸模之间的缝隙在铸造时产生突起的模线也被保留下来。随后这些铸件和作品中所需的电车铁轨经过陆运到达威尼斯。 博伊斯在翻制现场 博伊斯选用艺术中长期以来“不受欢迎的材料”——铁,除了他用铁象征男性外,同时也是基于童年记忆对莫里茨亲王的致敬。博伊斯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谈到童年的这一重要经历,莫里茨整体规划的克雷武一带,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他意识到人们可以用材料表现如此宏大并且对世界有决定性作用的作品,或者说整个世界依赖于一些小块物质状态,依赖于他们的处境和相互间的关系。博伊斯时常在迫击炮筒上坐很久,思考这些埋在过去的土地中又探出来张望现在的铁件。 人类演说家 从饰有龙头的炮管里发射出的人头,身体仿佛还禁锢在炮管中,表情痛苦,似乎正在呼喊。这位为自由和理想殉道的雄辩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卓有远见的政治人物科娄兹。年科娄兹出生在克雷武附近一个有荷兰血统的普鲁士贵族家庭,二十岁时他结束了军旅生涯定居巴黎,并在那结识了卢梭和伏尔泰。法国大革命爆发初期的公开演讲让他成为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之一,同时自称“人类演说家”。由于反对君主制和教会,科娄兹放弃了贵族称号,并把自己的基督教名改为一位六世纪自然哲学家的名字。但随着大革命的发展,建立世界共和国的革命乌托邦理念使他越来越明显地与大多数革命者之间产生了根本分歧,最终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受到了公开攻击。科娄兹的国外出身也使他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最终革命法庭判处他死刑,他随即在断头台从容赴死。炮管上的头像首先让人联想到战争带来的不幸以及为革命献身者的思想。不同于罹难者的解读是,英勇无畏或者野蛮粗俗或者作为古代偶像,未淬火处理的粗糙头像如同流传于世的公元前二世纪的木质偶像雏形。 《有轨电车站》细部 斯拉夫木质偶像前二世纪 科娄兹激进的政治主张,出众的口才和坚定的信念所散发出的巨大魅力深深吸引了博伊斯。早在年博伊斯在罗马的展览“竞技场”开幕式上就做了题为“阿纳卡西斯·科娄兹”的朗读,这表明博伊斯和科娄兹两人相似的坚毅个性不仅来自他们共同的出生地,而且博伊斯在科娄兹的主张中找到了思想上的连接。穿着制服外衣的博伊斯在朗读结束后向前向左向右各鞠一躬,和科娄兹登上断头台前所做的告别动作一样。对博伊斯来说,科娄兹是第一个提出真正民主理论的人,博伊斯在日后也沿着这一政治偶像的斗争方向进行了各类实践。所以博伊斯也把这铸铁头像当作自传式的作品,并且再次出现在临终前回顾自己一生的总结性作品《王宫》(PalazzoRegale)中——关乎国家统治的思想,首先是征服,接着是有尊严地住在宫殿里,而其中的头像象征着我们的头脑。 博伊斯手持科娄兹传记 《王宫》 关于这个头像的诞生还有一段轶闻,据博伊斯的学生莎莘回忆,她做这个泥塑头像很久,起初是一个头戴花环的女性肖像,但她并不满意,于是去掉了花环和长发改成一个男性形象。随后博伊斯做了一些修改,这名学生觉得这个泥塑头像已经完成了,便放置在教室角落,直到某天博伊斯把这个头像夹在胳膊下面带走了。她后来才听另一个同学说头像被用在了博伊斯的作品中,但她表示这一做法对博伊斯来说似乎并不奇怪,因为他把他的学生们也看作是自己的作品。当然博伊斯对原来的头像继续进行了较大改动——嘴巴张开,嘴角上翘,眼眶加深,鼻梁增高——也就是说头像所传达出的痛苦表情全部来自博伊斯的塑造,因此也并不能算作是对学生作品的侵占。 《铁人》 未来纪念碑 最初由威尼斯建筑师东吉设计建在年倒塌的圣马可教堂钟楼废墟上的威尼斯双年展德国馆,在年第三帝国接管后,二十九年前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被德国建筑师海格加以改造:为使展馆更能给人一种纪念碑式的印象,彰显第三帝国建筑的恢宏,原本的多立斯式柱子被四根巨大的方柱取代,上面放置一个没有山墙的矩形楣梁。年联邦德国由于财政限制不得不搁置了外部重新设计的方案,最终在十四年后仅进行了小规模的内部翻修。翻修使得中央主室和半圆形后室之间隔墙被拆除,从而给予主室一种神圣肃穆的特质。博伊斯形容德国馆是“军官俱乐部和飞机棚厂结合的奇幻产物”。在此基础上,博伊斯还保留了墙皮脱落的斑驳和水渍发霉的污迹,甚至是墙上贴着的前次展览中里希特的作品标签,此举更增添了一种强烈的病态感。 威尼斯双年展德国馆近影 顶端带有头像的长炮管和四个迫击炮筒按原本的排布被竖立在方形主室中央,观众通过建筑正面的门可以直接看到表情痛苦的人像。博伊斯将一段略微弯曲的电车铁轨埋在旁边,铁轨上面露出地面,暗示着一个巨大的延伸到地下的圆,一方面致敬了莫里茨亲王的座右铭“向整个地球延伸”,另一方面博伊斯也延续了在早年为费茨·尼豪设计的墓碑中呈现的概念,地上墓碑的弧线可以由想象的地下世界部分补全成一个圆,指向时间的周期或者生死的轮回。在半圆形的后室部分,如同博伊斯深挖自己关于克雷武的童年记忆和故乡历史,一个透过层层时间沉积的孔洞向下钻过第三帝国改建的展厅地面并贯穿中世纪教堂钟楼的废墟直到威尼斯地下潟湖的水面,孔中插入的一根长杆由数小段连成并在地上部分两次弯折形成摇柄,钻孔的土渣堆在指向天空的炮管和孔洞之间形成一个小丘,加上从高处窗户射入的阳光,为作品增添了四个元素:天地水火。 《有轨电车站》 费茨·尼豪墓碑 通常指向历史事件的“纪念碑”是为了呼唤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丘比特柱”建立时传达的除了对往日战争的纪念,更有后世和平的愿望。作为副标题的“未来纪念碑”同样将两个表面看似矛盾的词语连在一起,这基于博伊斯对历史的见解——未来的远大抱负由昔日的教训和当下的苦难困境共同构成,也就是说通过反思历史和剖析今日的问题从而找到未来的出路。他在表述自己的目标时说,人们不会回到从前旧的认知体系,而是迈向未来扩展了的新认知体系,因此已经用尽的旧的认知层级将纳入新体系中。 博伊斯坚持这件作品只为威尼斯双年展树立一次,所以展览结束后,这一作品作为自身的剩余物被保存,再也没有被竖起过。收藏中有两个版本:阿纳姆库勒-穆勒博物馆收藏了双年展撤下来的版本,四个迫击炮筒首尾相连与放在地上的长炮管以及铁轨平行;另一个版本收藏在柏林汉堡火车站美术馆,长炮管垂直放在平行并排的三个迫击炮筒上,另有一个跑击炮筒立在前面,原来的铁轨被一段带转辙器的岔轨代替,或许暗示着对未来道路走向的选择。 阿纳姆收藏版本 柏林收藏版本 订正: 前文“曼雷萨”(上)中所述“五旬节门”上的棕色十字和“教皇门”上的半十字毛毡是添加在博伊斯年为展览“我的科隆大教堂”创作的大照片上,并未和年原门施工时博伊斯使用剃须镜一样真实出现在教堂南面大门上。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asaoa.com/nsjc/8173.html
- 上一篇文章: A客机着陆后冲出跑道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