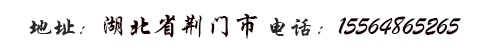危机下的变革明代后期战术及训练的发展与西
|
16—17世纪,由于火器性能的提高及普遍装备部队,中西方军队都已将之大规模投入战争。而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口,中西战术及训练的发展于世纪逐渐显示出不同的前景:前者斜阳西沉,后者却旭日初升。 明代后期军队的战术及训练:以“戚家军”为例 早在宋朝时期,中国就已将火药武器投入战争之中,但明代“火器的发展为历代所不及”。明初,就已有部分火器装备军队。洪武十三年,朱元璋规定每百户的武器配备为“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永乐年间,朱棣还组建了专门使用火器的神机营,并规定布阵方式为“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战斗之际,首以铳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坚,敌不足畏也”。明代中后期,南有倭寇骚扰,北有蒙金侵边,国家时常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现实的迫切需要,成了吸收西方军事技术发展火器装备的主要动力。随着火器的发展,明军的武器配备与兵种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戚继光镇守莉门时的部队,单以战斗步兵而论,其使用鸟铳的人数已经占到50%了,而且是单独成建制的火器部队。相比之下,西班牙军团作为十六世纪后期欧洲的代表性军队,其持火枪作战的士兵仅占战斗人员的30%左右。 军队装备及兵种结构上的变化必然伴随着战术上的演变。仍以“戚家军”步兵为例。这种结构中的队、旗、局、司、部、营已经大致相当于班、连、营、团、旅的现代军队编制,鸟铳手则被独立编组为类似于连的单位。由于戚继光强调“夫营阵之法,全在编派伍什队哨之际”、“各色阵法皆在于编伍时已定”的编制同战术相结合原则,所以火器队与杀手队必然分开战斗。前者以轮流放铳法进行射击,即第一排射击完毕退至队伍最后装填,第二排跟上射击,再退至最后,周而复始。当敌军稍近时,火器部队则退至冷兵器阵列之后,由后者以“鸳鸯阵”准备接敌肉搏。参见图。这一队“鸾鸯阵”既是步兵最小编制单位,也是基础战斗队形,再由之组成全军的战斗队形。 战斗时,“火器在前,抬营而进;或寇来冲我,或列阵待我,挨到五十步内,火器听中军令齐发,……兵士乘火烟如云,一齐拥进;须是飞走,密布长器,如锋丛蚁附一齐拥上,不可毫发迟疑;短兵救之,无有不胜”。 此外,该阶段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为抵抗北方游牧骑兵而兴起了组建车营的热潮。所谓车营,就是配备了火器战车的部队。这种战车内载火炮,前方或左右设有防护板,平时可运火器,战时则以炮击敌,以车护炮。戚继光认为战车相连“一则可以束部伍,一则可以为营壁,一则可以代甲胄,敌马拥众,无计可逼,诚为有足之城,不秣之马也;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废,车何能御”。可见,车营实为火炮部队与步兵的混编单位,并须与骑兵协同作战为常规。其战斗程序一般为:当敌军进入米内外,车上佛郎机幵火齐射,火箭继而举放;待敌至米左右,骑、步、车兵内各鸟统手齐射,并与火炮、火箭交替射击,保证火力的周而复始、更番不歇;若敌仍不退,则施放虎踏炮;骑兵队出营,依次以鸟铳、火箭、弓矢轮流射击。若敌人即将近身,则铳手退至最后改换长刀,列鸳鸯阵与敌短兵接战;最后与骑兵实施追击。 显然,车营作战的核心是各种火器的连环施放,以求于敌军近身前便将其击退。因此,火力战在整个战斗过程中的地位已越发彰显。另外还可以发现,传统密集的大规模方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各级编制为基础的一个个小型战斗队形;以往大集团冲撞格斗以决定胜负的简单模式,变成了先火炮,继而火箭,再而火铳、弓箭,最后短兵相接的多层次打击输出。不过,由于战斗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包含着更多的技战术环节,故而每一个士兵都需要具备比过去在大方阵中更娴熟的操作技术和更默契的协同配合;对于指挥官来说,控制步骤如此繁复的战斗过程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世纪西方战术及训练变革 同一时期的欧洲,火绳枪已经成为作战中不可或缺的武器。“16世纪的军队倘若手里没有火枪,它是决不敢跟有火枪的军队交战的”。但最早真正意识到火器巨大潜能的是西班牙人,他们相信火绳枪能够在战斗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西班牙人较早放弃使用弓弩而偏爱火绳枪”,并且于16世纪的下半叶采用了一种重型火绳枪。但由于这些早期火器射击精度差、射程有限,尤其是射击速率太低“每三分钟发射二发子弹就是极好的了”,如何才能在脱离了防御工事的野战中既有效保护火枪手,又能使之发挥出更大的火力,成了此一武器能否在战斗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关键问题。 意大利战争年年的检验证明,西班牙方阵较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西班牙方阵在成熟阶段完全以长矛取代了原来的剑盾兵和戟兵,使其同火枪构成了固定的组合。每个方阵的纵深为20列,正面为50——60人。方阵外围和四个角上部署着排成密集方队的火枪手,以反向行进装弹法进行射击,从各个方向提供连续的支援火力。当火枪手受到近身威胁时,他们便躲到长矛方阵所组成的防御墙之后。3个这样的方阵组成1个步兵团,成前后错幵的棋盘格式布列。 这种提高火器战场效能并以此为目标建立一种新战术体系的努力,使西班牙军团在16世纪成了欧洲最令人生畏的野战部队和各国竞相效仿的对象。这一体系进一步确保了步兵在战场上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提升了火器在野战中的杀伤效能。由其所创造的长矛加火枪的武器系统,成为了之后两个世纪里西方战术演进的基础。 西班牙方阵的问题在于,由多人组成的一个方阵作为基本战术单位显得过于臃肿,要在机动中保持队形的完整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外,它还存在着浪费兵力的问题。处于方阵深处的士兵只能像局外人一样无所作为,而那些居于方阵后部的火枪手,也只有当敌军攻击其侧后时才有用武之地。不少西班牙军官都曾对这一战术体系进行实验和改造,力图达到对火力的最佳使用效果,但都没有拿骚的莫里斯的革新那么出色。 拿骚的莫里斯,即奥伦治亲王,荷兰著名的军事统帅。为了抵抗西班牙大军的入侵,莫里斯从古典军事著作中汲取教益,在模仿古罗马军团战术及训练模式的基础上对荷兰军队进行了根本上的变革。他取消了庞大的步兵方阵,代之以一个约人的营作为基本战术单位。 其中长矛兵部署为50人正面、5人纵深的横队。火枪手则单独列阵于长矛横队的两侧,而非以往那样混合于方阵之中。每侧配有三队火枪手,每队正面4人,纵深10人,同样以反向行进装弹法进行战斗。另有60名火枪手被预留出来作为散兵火力。这些营被部署成像罗马军团那样前后交错的三条阵列。这种浅纵深的战斗队形被称为“莫里斯横队”,是为后风靡欧洲的线式列队的雏形。其优越性就在于,在更多士兵可以投入到战中去的同时,还可以留出预备队以运用到关键位置。而战术单位的小型化则使这种灵活的调动成为可能。 另外,火枪威力也得到了更有效的释放,进而战斗虽然仍以白刃格斗决定胜负,但火力杀伤的效果则越来越影响着近战的成功与否。因此,在这个新战术体系中,火力和突击得到了真正紧密的结合。正如美国军事学家杜普伊的评论:“摩利士(即莫里斯)对战争艺术的主要贡献就是从最佳的战术角度来使用兵力。” 不过由于这样的体系需要下级单位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所以也就需要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低级军官。为此,莫里斯在部队中配备了较高比例的军官和专业军士,让他们有较多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这也是莫里斯“一直被称为现代欧洲军官团的鼻祖”的原因。此外,“指挥这样的战斗要求在战场上有高度控制的能力:控制行动,控制火力,更重要的是自我控制”,所以训练和纪律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在这一点上,莫里斯也作出了一项影响至今的变革:推行系统化、标准化的军队操练。在当时多数的军队中,训练往往只限于教会士兵们如何使用武器。但莫里斯追求更加稳定和有序的控制。他将火枪复杂的装填、发射过程分解为42个连续的、具有固定标准的动作,规定了每个动作的名称和口令;同时,他还使士兵按照规定的步伐和节奏行进、转向以及变换队形。通过这种形式的反复操练,士兵的每个动作都接近了半自动化的程度,从而减少了因自行其是或战斗紧张所造成的混乱,将出现失误的几率降到了尽可能低的水平。 如此一来,不仅射击速率得到了提高,而且由于士兵的射击和行进的每个动作都可以控制,指挥官们便能下达更准确、细致的命令,从而实现士兵之间、战术单位之间实现更紧密的战斗协同。这就为战术单位的小型化提供了相应的控制指挥体系。再者,反复的标准化操练还有一个隐性的意义,那就是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灌输纪律意识和服从观念。“动作被分解成各种因素。身体、四肢和关节的位置都被确定下来。每个动作都规定了方向、力度和时间。动作的连接也预先规定好了”;因而标准化操练也就是一种将动作行为符码化的身体规训,它“从一切事物中专横地排除任何观念、任何低语,训练有素的士兵开始服从任何命令,他的服从是迅速而盲目的”。这种训练的效果就是“即使在大炮的唯哮下,在火枪的呼下,在云团一般的白烟翻滚下,即使在左右的战友纷纷倒下,伤兵哀号四起的情况下,部队仍能像机械一般精确地前进和齐射”。 这些训练标准还被编撰成《荷兰条令》,显示出了近代“操典”的雏形。“这使得所有的指挥用语,以及长矛、火绳钩枪和滑枪枪等武器的指南都有了规范”。年,拿骚的约翰内斯二世莫里斯的表亲,委托一位名为雅各布德格恩的幽家将新式操练中火枪手和长矛兵的每一个分解动作都作出图示。年这些图解成书出版,其中还附有相应的口令。军官和士兵都可以借此清楚地了解各种动作的操练方法。但莫里斯很快又意识到,标准化的操练是以标准化的武器为前提,因此开始为其军队装备统一的武器。在他和他的表兄弟们的协助下,荷兰军队的标准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所有为荷兰效力的军队都装备着相同长度的长矛,相同样式的盔甲,以及最重要的,相同型制的火枪。 这种由战术变革所引起的操练和武器的标准化努力,隐约显示出了火器大量运用所带来的战术本质上的微妙变化。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指出了新体系的特点:“莫里斯为操纵滑腔枪和长矛制定出流程作业图,并对行为序列的每一细节都给予了明确的说明。士兵们必须实践这些流程,直至他们能自动地遵循‘正确的’程序。新兵们不被看成是能熟练使用武器的‘手艺人’,而被看作是一些为了熟练地操纵军事装备而需要接受训练的人。”这就意味着在此一体系中,士兵单人娴熟的作战技能和灵活的身手等个人主义表现,已经逐渐让位于提高整个战术单位效率所需要的操作规范。这就不能不让人把它同世纪初的泰罗制度(或称泰勒主义)联系起来。其基本思路是:“每个行业的每个具体活计上所使用的众多办法和工具中,往往有一种办法和一样工具比其他任何的办法和工具要更好些。 要发现这个最佳办法和最佳工具,只有通过对一切在用的办法和工具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结合着进行准确的、精密的动作和工时研究。”有基于此,泰罗认为只有将计算和实验得出的最佳办法和最佳工具定为标准,据以严格规定每个人的动作,从而取代工人们的习惯——因为基于经验的习惯做法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才能保证操作速度得以加快。这也是他所提倡的科学管理模式的第一要素。:不难看出,莫里斯所创造的系统化、标准化操练,在本质上和泰罗制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说明,西方的战术——至少是与武器技术相关联的那一部分内容,开始逐渐显露出了理性分析和计算的特征,越来越朝着工业化时代那种追求效率的合理组织形式与管理机制的形态演变,而不再是将军们于个人经验基础上的奇思妙想。作为训练和战术科学化、规范化的标志,西方军队的操典、野战条例等标准正是由此逐渐演化而来。这对于世纪欧洲战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乃至整个西方军事科学体系的建立显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许多西方军事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用精密的分析系统的综合来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则”。 不同的走向:中西比较及启示 相较而论,这一阶段中西战术的整体样式可谓大致相符。双方都在寻求构建既能充分发挥火器战场杀伤力,又能有效保护火器手免受骑兵冲突的战术体系。双方都不谋而合地运用了后退装弹的轮番射击战斗程序。队形上的区别也仅在于,前者火器手居前、冷兵器手居后成纵深配置并以战车组成方阵,后者则以长矛方阵或横队遮蔽火枪手并将两种武器成一线配置。因此在战斗队形、战斗程序上,两者并无判若云泥的先进与落后之别。若就火器的运用来说,明军以火炮、火箭、火铳所组成的多层次火力打击显然还要更为精巧。 不过,精妙的战术设计与高效的战场运用并不能立即划上等号,因为越是复杂的体系,其出现故障和混乱的概率也就越高。正如杜普伊所提醒的,应“尽力使自己的军事行动与兵力组织计划趋于简单,在千军万马务必协同动作完成一项计划的情况下,即使是最简单的计划也可能会失败。加之在战斗过程中一旦官兵发生惊惶与骚乱,混乱与失败的可能性就会变得更大。”火器的大规模运用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技术细节与装备要素,则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显著。“军队战斗力的强弱愈发决定于人与武器的配合。 例如,对步兵营来说,战斗中的胜利大体上同火枪手能否快速地通过装药、装填和射击的复杂程序与装备带刃兵器的人员在不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向前运动的速度成正比。”因此,要确保火器能够稳定地齐射、多层次地紧密衔接以及实现火器手与冷兵器手能够精确地协同配合,标准化的训练就势在必需。这正是西方前近代军事领域最重要的一项改革。缺少了这一点,即便士兵在平时训练中技艺娴熟,也不一定能在確烟弥漫、人喊马哪的紧张环境中发挥出既有的水平,而精密的多兵种协同战斗则更无从谈起。戚继光反复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平日教场操演,乃无利害之地,从容中节,便可为用。若临阵,生死目前,心忙手乱,每致火药自焚。” “平时在教场操时,打铳则把托稳定,对把从容;舞械则以单对单,前无利害,似谓习之已精已至矣。临敌之时,若使仍是照前从容剛应,如教场内比试一般,不必十分武艺,只学得三分亦可无敌。奈每见时,死生呼吸所系,面黄口干,手忙脚乱,平日所学射法打法尽都忘了。……或乎向前放钪而头已回顾走路,或忘入始子,或下始子而后入药,或装毕而灭其火绳,或湿其药线,或自焚其药,十铳之中仅有四五统发出,四五之中仅有一中为难矣。” 但他似乎并未采取标准化训练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最接近的措施为其所编施放鸟铳和虎縛炮的《铳歌》。鸟铳的《铳歌》写道: “一洗铳,二下药,三送药实,四下裙子,五送销子,六下纸,七送纸,八开火门,九下药线,十仍闭火门,十一听令开火门,照准贼人举发。” 然此仅为装填与击发鸟铳十一个步骤的一般性说明,而非具体的动作规范。所以在操作的过程中,主要还是依靠士兵个人的经验和习惯。至于其他武器,平时所进行的也是一种个人武艺、技艺的训练。说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实际上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操典,因为操典的本质,就在于逻辑分析的思维方法去总结实战中最有效率的方法,并将之以明确界定的术语表达出来,作为全军的操作标准。 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另一个问题:战斗指挥。双方都趋向于战术单位的小型化,但不同的是,莫里斯在缩小编组的同时赋予了这些基层单位指挥官更多的自主性。而戚家军则缺乏这种基层的指挥,任何方向上的任何战术动作都依赖于中军的鼓号、旗积发令。例如其规定: “铳手虽列于外,专听中军号铳,中军主将自掌号统,看咸至五六十步中军放号铳一个,向贼一面才许放铳,分番如期,每长声喷,放一次。看中军放起火一枝,方许一体放火箭,如无号铳,便贼到营下亦不许轻放。” 这就有可能产生两大弊端。一是命令的延误。而由主将发现情况作出决断,然后以号铳、信炮等工具下达命令,再到士兵听见或看见信号执行命令,显然是一个颇费周折的过程。然而战场机会转瞬即逝,此一指挥程序很有可能错过最佳行动时机。若考虑到声音传播的延迟和战场上“烟火瘴蔽”导致视线受阻,以及火器发射需要时间等细节因素等,其中的延误可能还会更为显著。未能在正确的时间开火,也就意味着失去使用火力的最佳机会,火器的优势也就因此大打折扣。二是指挥的准确性。火器的多层齐射和小型单位的战术机动,需要指令精确细致,而喃卩八、旗鼓、信炮等工具,显然无法对基层单位的具体战斗行动进行指挥。因此,若无像俞大猷、戚继光等对军队具有极强控制能力的将帅,此种战术的弹性与效果也就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战术作为战斗的方法,往往于细微处见高低。因为战斗的基本原则、规律并不难理解。最难的是如何使既有武器系统发挥出最髙的战斗效率。缺失标准和规范,是明军实施其战术构想的最大障碍。若就整个明代军队建设而论,情况亦是如此。例如早在洪武元年时,西平侯沐英征百夷思伦,就曾“下令军中置火铳、神机箭为三行,列阵中,俟象进,则前行铳箭具发。若不退,则次行继之。又不退,则三行继之”。 可见明初即有轮流齐射的火力打击方式。而正统十四年土木堡惨败后,户部给事中李侃便提出了以车对骑的战术:“取(骤车)为战车,车列四周,步骑处中,车厢兼用铁索连木板,藏神铳于内,俟交阵始发。每车刀牌手五人,乘间下车击敌,敌退则开锁纵骑逐之。”此则为明代火器战车以及车骑步联合战术的滥缩。景泰元年,京营五军坐营都指挥佥事王淳则设计了以长刀、长枪和盾牌掩护的火铳、弓箭手居前,骑兵居后的战斗队形,以及“敌在百步之内,神机枪射之;五十步之内,弓箭射之;二十步内,牌枪刀迎击”的战斗程序。 由此可见,冷热兵器相结合的战术思路其实早已有之,但似乎直到明代中后期却仍未制定一套推广全国的战术标准。反而往往是不同将领主持军务,便各自推行基于个人经验和偏好的武器配备、训练方法。例如从嘉靖时期的刘天和、曾统、俞大猷的战车,到隆庆时期的戚继光的车营以及俞大猷所练京营战车,再到明末孙承宗的战车,均有不同的武器配备和人员编制,且其中多数都投入了生产并装备部队。因此,虽然看似战术不断翻新,但基本思路却也不外于以车御骑、火器迭放这一原则,而武器和训练未能标准化、指挥系统和后勤体系未能完善等问题却基本上延续了下来。 此外,由于新人上任则推翻重来,前此所投入的大量财力、物力皆成虚掷,军队训练也无法形成长期性和连续性。当然,这同明代复杂动荡的政治局势有莫大的关系,不能完全归因于军事领域。而且如黄仁宇先生指出,明朝火器制造停留在农村技术的水平上,不可能是标准化的,必然会对军队——例如戚继光的部队,产生战术上的影响。但也不难发现,即便如戚继光这样被中外广泛称誉的将领,似乎并未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施武器、训练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 就军事领域而言,思维方式上的异趣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西战术发展,在细节层面上已经体现出双方思维上的不同偏好:前者更多地依赖于将领和士兵基于经验的创造,而后者则更注重逻辑分析方法以寻求最有效的方法。更进一步说,隐藏在武器和训练标准化背后的,其实就是一种近代科学理性的精神。中西军队在这方面的差距或许正是双方同样将火器广泛投入战争之后,战术及训练发展水平却此消彼长的一项隐性因素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asaoa.com/nszs/10004.html
- 上一篇文章: 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姐妹大公,姐姐活到30岁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