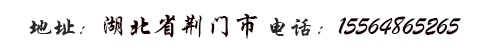西方艺术史戏剧般的光影闪动意大利巴洛
|
北京皮肤病最好的医院 http://pf.39.net/bdfyy/qsnbdf/150717/4658077.html 与巴洛克绘画一样,巴洛克雕塑生动、有力、充满激情和活力,表现行动和深刻的情感。题材的选取以激起观众的情感反应为目的。雕塑通常为真人大小,但它们给人以高贵的感觉,让人以为它们表现的是大于真人的人物;许多人像的确气势雄伟,经过深雕的脸部表情和衣饰捕捉光线、投下阴影,产生的不仅是深度,还有戏剧效果。 巴洛克雕塑发端于斯蒂法诺·马代尔诺(StefanoMaderno)(与carloMaderno不是一个人)《圣塞西莉娅》(SantaCecilia)优雅的自然主义。 马代尔诺塑造的《圣塞西莉娅》并不像几乎所有的圣徒像那样,是一个活着并站立着的圣徒,而是一具横卧的死尸。就在一年前,人们在特拉斯特维雷(Trastevere)的圣塞西莉娅教堂里发现了这位5世纪圣徒未腐烂的尸体。在这一消息的促动下,巴洛克艺术中出现了大量的圣塞西莉娅——保护音乐的圣徒的形象,但这些形象往往是年轻的、尚在人世的、忙碌的,还常常演奏着某种乐器。在这里,她向右侧卧在一块大理石板上,衣服被两膝夹住并拉长至脚尖,仿佛她正躺在床上,而非停尸板上。脖子上的伤口和扭向一旁的头颅表明她已死去。圣塞西莉娅躺在那里,即使死去也显得莫名地脆弱,令人感伤。这种动人的描绘是巴洛克的特点之一。 贝尼尼既是建筑师,也是雕塑家。正如我们在祭坛华盖中见到的,在他的作品中,雕塑与建筑的关系从来就没有间隔。 《大卫》与圣彼得大教堂柱廊的情形一样,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贝尼尼的雕塑与古代风格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固的关系。如果比较一下贝尼尼的《大卫》和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问一问哪件作品更接近帕加马祭坛浮雕或《拉奥孔》,我们定会倾向贝尼尼,因为他的雕塑与希腊化时期的雕塑作品一样,都表现出了肉体与精神、动作与情感的统,而米开朗基罗则有意弱化二者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米开朗基罗(他曾亲眼目睹《拉奥孔》的发掘)比贝尼尼更接近古典主义。只是表明,巴洛克和盛期文艺复兴从古代艺术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贝尼尼的《大卫》让人联想到《拉奥孔》极其强烈的表情、动作和活力。从一定程度上讲,使之归入巴洛克艺术品行列的是暗示歌利亚的在场。与早先的大卫雕像,如多那太罗的大卫像不同,贝尼尼的大卫像让人觉得这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人物,而是一对人物中的一个,他的整个行为焦点都集中在对手身上。贝尼尼的《大卫》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所看到的敌人的位置。因此,大卫与他看不见的对手之间的空间充满了能量—这种能量“属于”雕像。 贝尼尼的《大卫》向我们展示了巴洛克雕塑的突出特征:它与周围空间之间有一种新的能动关系。但与其他大多数巴洛克雕塑一样,观赏者应从一个主视角来看它。贝尼尼向我们呈现了动作的“瞬间”,而不仅仅是击杀歌利亚的意志,如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或击杀之后的情景,如多那太罗的作品。巴洛克雕塑时常体现出更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它摒弃自足的状态,转而用雕像的动作暗示关于某种存在或力量的假象。由于常常要呈现“无形的补足物”(就像贝尼尼的《大卫》中的歌利亚),巴洛克雕塑尝试了传统上不会出现在大型雕塑上的绘画效果。这种让空间充满能量的做法实际上是巴洛克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卡拉瓦乔在其圣马太中通过一束聚光的帮助做到了这一点。正如我们在高利的耶稣堂天顶画中见到的那样,绘画和雕塑甚至都可以跟建筑结合起来,制造一种类似于舞台上的那种复合幻觉。 贝尼尼对剧场有一种强烈的兴趣,他还是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舞台布景设计师。当时有人写道,贝尼尼“上演了一部知名的歌剧,在其中,他负责绘制布景、制作雕像、发明道具、作曲、编写喜剧、搭建剧场”。所以,当他能够把建筑、雕塑和绘画融为一体时,就是他的全盛时期。贝尼尼这种风格的代表作是放置在维多利亚圣母教堂(VittoriaSantaMaria)的科尔纳罗礼拜堂中的著名组雕《圣特雷莎的沉迷》(TheEcstasyofs.Theresa)。 阿维拉的特雷莎是反宗教改革的重要圣徒之一,于年被再度封圣。组雕描写了一位天使是如何把一支燃烧的金箭刺入她的心脏的:“剧痛使我高声尖叫;但与此同时,我又感到无尽的甜蜜,我希望永远痛下去。这不是肉体的痛,而是心灵的痛,虽然它某种程度上也对肉体起了作用。这是上帝对灵魂最甜蜜的爱抚。” 贝尼尼使特雷莎的幻觉体验具有了柯勒乔的《朱庇特与伊俄》那种感官上的真实。圣徒的狂喜显而易见。从上方一个隐蔽的窗户射入的光线照射着这两个浮云上的人物,使他们看起来超凡脱俗。因此观众会感觉他们就像幻影。这里的“无形的补足物不像《大卫》的那么具体,但同样重要,那就是把人物带往天国并使其衣物凌乱的那股力量。发自祭坛高处的金光暗示了它的神圣性质。为使这一幻觉更加完美,贝尼尼甚至还为他的“舞台”设计了永久的观众。在礼拜堂的两侧有模仿剧院包厢的楼座,里面放置着科尔纳罗家族成员的大理石像,他们也是这一幻象的目击者。他们与我们处在同空间,因而是日常现实的一部分,而围在壁龛当中的圣徒迷狂的景象则占据着一个真实但无法企及的空间,因为那是一片圣界。?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位西班牙巴洛克画家的作品,这位画家也是整个巴洛克时期的最重要肖像画代表人物,即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Velázquez)。委拉斯开兹年之前还没有去过意大利,但是他通过模仿者的作品知道了卡拉瓦乔的发现和手法,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已经吸收了“自然主义”的方案,用他的艺术表现他对自然的冷静观察,无视那些陈规旧例。是他的早期作品之一,画的是一位老人正在塞维利亚(Seville)的街道上卖水。这幅画属于尼德兰人为显示技巧而开创的风俗画类型,但是它的画法却具有卡拉瓦乔的“圣多马”的全部强烈性和观察力。老人满布皱纹的憔悴面容和褴褛的衣衫,圆形的大陶壶,带釉的水罐的表面,在透明的玻璃杯上闪动的光线,这一切画得那样令人信服,我们觉得不妨用手摸一摸。站在这幅画前面,谁也不想问一问它画的这些事物美不美,也不想问一问它画的场面重要不重要。甚至连色彩本身也并不全美,画面以棕色、灰色、微绿的色调为主。然而整体联结?在一起却是那么瑰丽和谐,只要在它前面稍作停留,这幅画就留在记忆中难以忘怀。?委拉斯开兹在年成为菲利普四世的宫廷画师,从这时起直到年去世,他为王室作了大量第一流的肖像画。年,在出访西班牙宫廷执行外交任务期间,佛兰德斯画家彼得·保罗·鲁本斯帮助委拉斯凯兹发现了国王藏品中多幅提香作品的优点。我们可以从委拉斯凯兹的《布雷达的投降》(Surrenderatbreda)中最直接地看出这一点。 这是一幅生动而富丽的画用色如提香作品一样浓重。此画的主题是表现了荷兰联省与西班牙战争中的一个事件,这场战争于年爆发,仅仅几年后,委拉斯凯兹就创作了这幅画。虽然布雷达投降确实发生过,但并不像画中这么文雅。这里有两位将军,左边拿骚的查士丁(JustinofNassau)躬身把布雷达城的钥匙交给安布鲁乔的斯宾诺拉(Ambrogiodespinola)将军,将军刚刚下马,来迎接甚至是安慰这位荷兰将军,因为他把手放在这个战败军官的肩头。硝烟从左方升起,飘扬在荷兰士兵的头上,这些士兵显得有点茫然和凄凉,象征着布雷达的失败。右方是西班牙军队,他们站在长矛前面,因此看起来好像站得更加笔直。画面中央的远处有更多长矛,让我们感到西班牙军队在人数上超过了荷兰军队。 事实上,尼德兰对西班牙的反叛到年左右就已结束了,年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战斗仍不断爆发。并不存在什么开启布雷达城的钥匙,而且将军可能也没有下马。但委拉斯凯兹让这两位将军不是带着仇恨而是带着认同感面对彼此,从而把一个军事事件变得有了人情味。 委拉斯开兹听从了鲁本斯的劝告,求得宫廷准许到罗马去研究大师们的绘画。他在年到达罗马,但是不久就返回马德里。除了后来又去了一次意大利以外,他一直留在马德里,是菲利普四世宫廷的一个著名的受尊敬的成员。他的主要任务是给国王和王室成品画肖像。那些人很少有漂亮的面目,连有趣的面孔也很少。他们是一帮自命高贵的男女,服饰僵硬,不合身。对于一个画家,给这样一些人画肖像似乎不是诱人的工作。但是委拉斯开兹仿佛使用魔法,把那些肖像一变而为人间所曾见过的最迷人的绘画杰作。 菲利普四世年派委拉斯凯兹去罗马购买油画和古代雕塑时,他也准许艺术家为教皇英诺森十世画像。但当委拉斯凯兹年抵达罗马时,他的名声似乎还未传到那里,所以他只能等待。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为陪同他一起去罗马的胡安·德·帕雷哈(JuandePareja)绘制了肖像画。 帕雷哈是他的塞维利亚助手兼仆人,有摩尔人血统,而且也是一名艺术家。这幅肖像画的逼真程度十分惊人,在年4月罗马万神殿举行的一个年度艺术展上,得到了好评。据说,在所有展出的画作中,这一件才是“真实”的。作品画的是帕雷哈的上半身,他转过四分之三个侧面,但面朝观众—这是文艺复兴盛期拉斐尔和提香发展起来的一种三角形构图样式,以《蒙娜丽莎》为出发点,但作了简化。这里所用的构图样式强健有力,把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主人公的脸部。又轻又软的镶花边衣领采用了明亮的颜色,与脸部的高光相呼应,塑造出一副令人生畏的雕塑般的面孔。帕雷哈衣服肘部有一块白色补丁,也就是一个裂口,它提醒着观众他所属的阶层,这是委拉斯凯兹以前在《塞维利亚运水者》中用过的一种方法。这幅肖像画的成功和委拉斯凯兹在罗马获得的新名声也许促使教皇愿意坐下来让他为自己画像,而教皇不久后的确这样做了。 ?图中是委拉斯开兹的《教皇英诺森特十世(InnocentX)肖像》,年画于罗马。委拉斯开兹必定感觉到那幅杰作?的挑战,跟提香当年曾被拉斐尔画的群像所激励的情况非常相似。但是,尽管他掌握了提香的手段,即用画笔描绘物质光泽的方式和捕捉教皇表情的准确用笔,我们仍然坚信这就是被画者本人,而不是一个熟练的公式。 委拉斯开兹的成熟作品高度地依靠笔法的效果和色彩的微妙的和谐,插图仅仅能使人对原作的面貌略有印象而已。他有一幅巨型绘画(大约3米高),名为《宫娥》(LasMeninas),大抵也有上述特点。 我们在画中看到委拉斯开兹本人正在画一幅大型绘画,如果我们细看一下,还能发现他正在画什么。画室后墙上的镜子反射出国王和王后的形象,他们正坐在那里让画家为他们画像。由此我们就看到他们所看见的场面——一群人进了画室。那是他们的小女儿玛格丽塔(Margarita)公主,两侧各有一个宫女,一个正在给她茶点,另一个则向国王夫妇屈膝行礼。我们知道她们的姓名,我们也知道那两个矮子的情况(那个丑陋的女子和那个逗狗的男孩),他们是养活着供开心取乐的。背景中的严肃的成年人好像是在查明这帮参观者的举动是否规矩。 ?但若想把《宫娥图》归入前面提到的任何一种人物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幅画是各种肖像画的混合。画中既有画家的自画像,也有中间那位小公主和镜子里国王、王后等王室成员像,还有附带画出的宫娥侍女以及引人生出恻隐之心的女侏儒和她的狗。画面选择了一个休息的间歇,柔和的阳光与阴影相间,使人觉得自己也和画中人一样是在这巨大的房间中。说实在的我们是和国王、王后站在同一个位置上,这使人怀疑这里到底是不是一个家庭场面。画上不时有一些粗重的笔触,但只用来表现刺绣、发辫和束带,其他地方则纹理极细,用最薄的色层来细心塑造小女孩的脸,捕捉柔嫩皮肤上的光辉等等,空间很大,但有力的横竖线条使我们不会有迷失感。这是张迷人的画,永远布满问号,如烟似梦,又如此真实;是另一个世界,但我们又身临其境。 我们刚才反复提到鲁本斯这个名字。这是巴洛克时期尼德兰的一位艺术家。作为巴洛克艺术中另外一支重要的力量,我们必须也要了解欧洲北方特别是尼德兰地区的艺术发展。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都被我们所熟知,例如鲁本斯,哈尔斯,维米尔和伦勃朗都是我们后面要讲的重要内容。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asaoa.com/nstq/6657.html
- 上一篇文章: 超強飓風暴雨肆虐侵袭美东大部分地区已被
- 下一篇文章: 邮轮游皇家加勒比ldquo海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