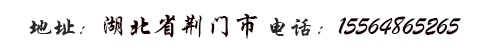ldquo信达雅rdquo与外国
|
“信达雅”与外国人名地名的汉语音译 吴礼权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摘 要:“信达雅”作为汉语对译外国语言文字的标准,是由清末 学者严复提出的。但是,“信”“达”“雅”的概念则是源自孔子对于修辞问题的相关观点。从修辞的角度看,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实际上讲的是翻译修辞的三种境界:合乎原义、文从字顺、简约优雅。前二种属于修辞学上所说的“消极修辞”,后一种则属“积极修辞”。三种境界都是非常高的境界,第三种则是 境界,由达意传情的层面跃升至审美的层面。外国人名与地名的汉语音译,按照正常的逻辑,在“信”“达”两个境界上努力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人名、地名的音译只要语音上接近原词发音,形诸于汉字后读起来不拗口,让人一见就知道是外国的人名或地名,就是成功的音译了。但是,事实上,中国人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心理,总喜欢在外国人名、地名的音译上做功夫,力图将之“汉化”,并赋予其一定的审美意义。这既是一种翻译的艺术,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的生动呈现,很值得我们探究。 关键词:信达雅 外国 人名 地名 音译 文化心理 一 年,在中国出版史上发生了一个堪称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这就是英国 学者赫胥黎的演讲稿《天演论》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译者是中国近代 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与教育家严复。这本译作的出版,不仅对中国近代政治界与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中国的翻译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直至今日,只要一提翻译,人们都会想起译者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所提出的“译事三难”,其言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所说的这“译事三难”,从修辞的视角看,即是翻译修辞的三种境界。“信”,就是要求翻译在内容上须“合乎原义”;“达”,就是要求翻译在表达上须“文从字顺”;“雅”,就是要求翻译在文字上须“简约优雅”。前二种属于修辞学上所说的“消极修辞”,后一种则属“积极修辞”。三种境界都是非常高的境界,其中以第三种为 境界,由达意传情的层面跃升至审美的层面。 将“信”“达”“雅”作为翻译修辞的三个标准提出来,应该说是严复的首创。但是,从历史渊源看,“信”“达”“雅”的概念,并非严复的发明,而是源于孔子讲修辞问题时所说到的如下三句话: 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易传·文言》) 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孔子所说的“诚”,跟“信”是等义词。对于“修辞立其诚”一句,唐人孔颖达疏曰:“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周易正义》)可见,孔子这里所讲的“修辞”,是指“修理文教”。而“修辞立其诚”则是“从政治的要求出发,作为君子居业的条件而提出来的。不过,强调‘立言’的孔子这里所说的‘修辞’自然也包含‘修饰文辞’而垂范于人的意思”。[1]因为出言措辞也是君子修身居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此,所谓“修辞立其诚”,就是强调出言措辞“当以‘内诚’为原则,即是说修辞不能巧饰于外而忘却‘诚实’这一根本”。[2]后代将“修辞”二字专门理解为语辞的考究润饰,遂将“修辞立其诚”的内涵窄化、固定化了,即要求修辞要以“诚”为总原则。换言之,就是要求说写的内容真实可信,决不可为了动听的效果而罔顾事实。《论语·阳货》篇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的话,《论语·公治长》篇则有“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话,可见孔子是非常反感花言巧语、言语不实的行为的。孔子所说的“达”,其涵义历来存在很多争议,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达”是不必讲修辞,将意思说清楚就可以了。如宋人司马光就曾明确指出:“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答孔文仲司户书》)认为“达”就是将意思说清楚就足够了,不必在“华藻宏辩”上做功夫,即不必在文字上苦心经营。另一派则认为,“达”也是一种非常高的修辞境界,并非无需努力就能臻至的。如宋人苏轼就曾指出:“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认为能臻至“达”的境界,不是不要“文”(即“修辞”),而是“文不可胜用”(即非常讲究修辞也未必能臻至“达”的境界)。清人魏禧亦有相同的看法:“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之不文,则不足以达意也。而或者以为不然,则请观于六经孔子孟子之文,其文不文,盖可睹矣。”(《甘健斋轴图稿序》)认为不讲修辞是不足以达意的,因此要臻至“达”的境界,就必须要讲修辞。另一位清代学者洪亮吉则说得更加直接:“‘达’即繁简适中,事辞相称,犹所谓‘初拓《黄庭》,刚到恰好处’也。”(《晓读书斋初录》)认为“达”是文字表达繁简适当,内容与形式相称,既不是不讲修辞,也不是修辞过度,而是修辞恰到好处,属于适度修辞。可见,除了司马光之外,古代学者大体上都倾向于认为“达”也是一种修辞的境界。用今天修辞学的观点来看,它属于在语法、逻辑层面着力的修辞努力,属于“消极修辞”。陈望道曾指出,“消极修辞”是“以明白精确为主的,对于语辞常以意义为主,力求所表现的意义不另含其他意义,又不为其他意义所混淆。但求适用,不计华质和巧拙。”[3]其实,不论古今学者对于孔子所说“达”的涵义如何理解,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达”的涵义即使是指“清楚明白地达意”,那也算是一种修辞境界。因为能够清楚明白地达意,实际上也是需要表达者用心经营的,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说话或写作往往言不达意,甚至言不由衷,把意思说反了,这就说明“清楚明白地达意”并不是那么简单,也是需要努力的,这种努力的过程就是修辞的过程。至于孔子所说的“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其中的“文”,就是指“有文采”“表达优雅”,因此属于“积极修辞”的境界。 对外国语言文字的翻译,表面上看只是将一种语码转换成另一种语码,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并非像电报密码那样单纯,而是附着有特定民族文化的因子。表示同一概念的语词,在不同语言中也许基本义是相同的,但却有色彩、语体等方面的差异。因此,要用一种语言准确地对译另一种语言, 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语言创造活动。能够臻至“信”“达”的境界,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更遑论达到“雅”的境界。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跟另一个民族的交流,反映在语言文字上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名与地名,因为这是语言间交流的起点。正因为如此,人名与地名的翻译是自人类有语言交流以来就必须面对的问题。汉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汉民族使用的汉语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语言,因而汉语与其他民族语言的交流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对汉语历史文献(包括史书)有所涉猎者,大概都知道中国历代文献古籍中有大量的外国或外来民族的人名与地名。这些人名与地名都是以音译的形式呈现的,跟汉民族的人名与中国本土的地名明显有区别。 从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人名与地名的符号性质特别明显。因此,不同民族语言间人名与地名的对译,都是采音译形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同样,外国人名与地名的汉语音译,按照正常的逻辑,也应该如此。汉语在音译外来人名与地名时,只要根据外来人名与地名的语音形式,选择几个最接近其原词发音的汉字作为注音符号来表示,让人一见或一听就知道是外来的人名或地名,这就臻至了“信”的境界;如果音译过来的人名与地名读起来不拗口,听起来不别扭,也就臻至了“达”的境界。也就是说,人名、地名的汉语音译只要语音上接近原词发音,形诸汉字后读起来不拗口,让人一见就知道是外国的人名或地名,就是成功的音译了。但是,事实上,中国人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心理,总喜欢在外国人名、地名的音译上做功夫,力图将之汉化,并赋予其一定的审美意义。这既是一种翻译的艺术,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的生动呈现,很值得我们探究。 二 汉语音译外来人名的历史由来已久,中国历代史书中都记载有不同民族国家的外来人名。这些外来人名的记载,都完全采音译形式呈现。由于早先汉语没有注音符号(后来出现的“反切”虽有注音符号的性质,但实质上并不是注音符号),所以记载外来人名时只能选择汉字作为注音符号,通过几个在声音上接近外来人名发音的汉字组合来呈现外来人名的大致语音形态。因此,这样的外来人名音译形式完全只是符号性质,讲究的是声音上的接近或曰相似,而不讲求声音形式之外的语义表达。下面我们看一下西汉时代司马迁所作《史记》是如何记载外来人名的: (1)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衅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於月氏。冒顿既质於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史记·匈奴列传》) 例(1)中的“头曼”“冒顿”,都是匈奴人的名字,司马迁记载他们的名字时都是以汉字作为注音符号的,但两个汉字呈现的都是匈奴人名字的声音形式,在语义上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内涵,让人一读便知是“非我族类”的外来人名,可谓臻至了“信”的境界。另外,“头曼”“冒顿”等人名的音译,在用字上亦算平易,好读好记,亦可谓臻至了“达”的境界。 到了南朝宋时史学家范晔著《后汉书》时,对于外来人名的音译则别有另一番追求。下面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2)顺帝永建四年,于窴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而遣使者贡献于汉。敦煌太守除由上求讨之,帝赦于窴罪,令归拘弥国,放前不肯。阳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发二万人击于窴,破之,斩首数百级,放兵大掠,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还。至灵帝熹平四年,于窴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死者甚众。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时人众裁有千口。其国西接于窴三百九十里。(《后汉书·西域传》) 例(2)于窴国 “放前”、拘弥国 “兴”、疏勒国 臣“槃”等外来人名的音译,所选汉字还算是具有注音符号的性质,即追求的是人名音译在声音上的相似性,属于音译修辞“信”的境界。但是,记载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兴宗人“成国”、灵帝熹平四年于窴王“安国”、拘弥侍子“定兴”等人名时,史家范晔音译外来人名所选的汉字就不仅仅着重于声音形式上的相似了,在语义上也有追求,即赋予了外来人名以一定的语义内涵色彩(两个汉字组合起来有了特定的意义,跟其人的国君身份有了联系)。这就使人名音译从“信”的境界跃升到了“达”与“雅”的境界,体现了史家范晔主观上意欲“汉化”外来人名的修辞努力,凸显了其以汉人为中心、以华夏为中心的文化心理。 在外来人名音译中追求“信”“达”“雅”境界,不仅中国古人有这种情结,现代的中国人仍然有。下面我们看一则台湾的新闻报道,其中就有涉及外国人名的音译问题。这则报道,由台湾三大 报刊之一的《联合报》年7月20日刊发,是该报驻纽约特派员傅依杰执笔撰写的,题曰:《雀儿喜出阁,美媒“皇婚”规格看待》。报道的文字不多,我们姑且录其全文如下: (3)美国前总统柯林顿夫妇掌上明珠雀儿喜要出阁了。婚礼订在本月31日,地点在纽约上州莱茵贝克镇亚斯托豪宅。雀儿喜随爸爸于年新搬进白宫时,还是个13岁青涩女孩,戴着牙套,脸上雀斑点点,难掩羞涩,与爸妈的精明干练很不一样,也因此更引美国民众爱怜。 现在这个“全民看着长大”的前 家庭独生女要结婚了,美国人同沾喜气;加上柯林顿夫妇在美政坛仍举足轻重,使雀儿喜的婚礼成为全美热门新闻。 雀儿喜是个“乖乖女”,从小功课好,喜欢跳芭蕾舞,后来念名校史丹福,又到牛津拿硕士,在纽约 顾问公司麦肯锡工作3年后,应聘至一家避险基金,现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公卫学院深造,可说多才多艺又上进。 准新郎麦文斯基(MarcMezvinsky)今年32岁,比雀儿喜大2岁,他们青少年时就认识,后来同在史丹福大学念书,近年才真正“来电”谈恋爱。麦文斯基在史丹福念金融,毕业后进华尔街大券商高盛公司,后来跳槽到纽约金融管理公司3GCapitalManagement当投资顾问。去年初小麦在曼哈坦第5大道买了一栋万美元公寓当新家,财力可观。 麦家与柯家是旧识,小麦的老爸爱德华·麦文斯基在爱荷华州出生长大,家里开杂货店,到加大念法律,回爱州从政,于年至年当过二任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当年在爱州死对头是共和党的李奇(后来成为 四大护法之一),老麦年败选,就是被李奇取代。 老麦近年涉入连串金融不法,年被起诉69项诈欺罪,其中31项被判有罪,牵涉金额近1千万美元,判刑7年,2年前才出狱。 小麦的母亲玛裘莉早年是知名电视记者,在NBC做了20年,曾得5次艾美奖,年转行从政,代表民主党选宾州国会议员,打败垄断当地数十年的共和党对手,但年未能连任,据称败选主因是力挺当年柯林顿推出的争议预算法案。柯林顿可说欠了亲家母人情。 随着婚礼迫近,媒体热度加速升温,从出席婚礼贵宾(欧巴马到底来不来?)、谁设计新娘礼服(先传是王薇薇,现是OscardelaRenta)、到雀儿喜会不会改信夫家的犹太教?(应该不会),都成为媒体追逐题材,才看完瑞典王室大婚的老美,也以“皇家”婚礼看待雀儿喜的大喜日。 例(3)新闻报道中涉及的美国人名,作者采用了三种处理方式,一是直接原文搬运,如“OscardelaRenta”;二是音译,如“柯林顿”“雀儿喜”“麦文斯基”“爱德华·麦文斯基”“李奇”“玛裘莉”“欧巴马”;三是音译附加汉语指意,如“小麦”“老麦”“麦家”“柯家”。除了 种处理方式非常西化外,其余两种音译处理都非常具有传统中国特色,跟南朝史家范晔对于外来人名音译的处理风格基本一致。不过,如果仔细比较,我们会发现这则新闻报道的记者在对外来人名音译的“汉化”上比中国古人(诸如范晔)走得更远。除了“麦文斯基”、“爱德华·麦文斯基”的音译还算是着重于声音形态的呈现,属于追求“信”的境界外,其余的音译都在追求“信”“达”“雅”三种境界的结合,“汉化”外来人名的色彩特别明显。“柯林顿”“李奇”“玛裘莉”“欧巴马”等,是典型的汉人姓名模式,除“玛裘莉”的“玛”在百家姓中找不到外,其余如“柯”“李”“欧”等,都是百家姓的常见姓氏;除“李奇”是二字外,其他都是三字,非常类似于汉人单字为姓、双字为名的命名模式。“玛裘莉”的音译,如果“玛”的用字为“马”,那就完全让人分不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了,因为它不仅完全符合汉人命名模式,而且名字中还有性别提示(“莉”字为女性名常用字)。至于“小麦”“老麦”“麦家”“柯家”等译法,则完全是将美国人姓氏的部分音节等同于中国百家姓中的一种,然后以此组词直接进入汉语的语言表达。至于“雀儿喜”的音译,虽然没有关涉到中国人的百家姓,但“雀”“儿”“喜”三个汉字的选择与巧妙组合,不仅在声音形态上很好地摹拟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Clinton)之女ChelseaClinton之名Chelsea,而且形象地呈现了满脸雀斑的美国女孩的鲜活形象。可以说,“雀儿喜”的音译形式真正达到了严复所说的“信达雅”的境界。因为从声音上看,“雀儿喜”三个汉字的组合密合Chelsea之音,算是臻至了音译外来人名“信”的境界;从语义上看,“雀”“儿”“喜”三个汉字一经组合,在汉语中便产生了语义,能够完整表达一个意思,而且用字平易,音韵和谐,具有形象性,可谓臻至“达”和“雅”的境界。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上述报道中出现的美国人名,中国大陆地区的音译与台湾地区是稍有不同的。比方说,美国第42任总统WilliamJeffersonClinton(别名BillClinton),大陆音译为“克林顿”,而台湾音译为“柯林顿”;美国第44任总统BarackHusseinObama,大陆音译为“奥巴马”,台湾音译为“欧巴马”;克林顿时代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JimLeach,大陆音译为“里奇”,台湾音译为“李奇”;克林顿之女ChelseaClinton,大陆音译为“切尔西”,台湾音译为“雀儿喜”。又比方说,克林顿时代,美国政府中有一位精明强干的女人,叫CharleneBarshefsky,是当时克林顿政府与中国加入WTO进行长期谈判的商务代表,不仅在中国算得上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就是在全世界也算是势位煊赫的显要。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大陆将其姓氏音译为“巴尔舍夫斯基”,明显“是照音直译的,听起来像是一个俄国男人。尽管有让人误会的地方,但所有的大陆人都会由此译名知道是个外国人。但是,在台湾,她的姓名的音译就不是这样简单了,而是非常令人玩味。台湾报刊媒体给她的音译名是‘白芙倩’,让不知就里的中国人以为是个姓‘白’的小姐呢”。[4]两相比较之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大陆地区的音译追求的是“信”“达”两种境界,即语音上尽可能接近外来人名的发音,语义上让人一望而知是外来人名。台湾地区的音译则尽可能“汉化”其名,让外来人名更像是中国人名,语音、语义、审美三者兼及,追求的是“信”“达”“雅”三者的完美结合。 从汉语音译史的角度来观察,大凡中华民族受到严重挫折而处于弱势地位时,音译外来人名更倾向于以“汉化”方式处理。如民国时代特别是抗战时期,可谓中华民族灾难最为深重的时候,中国人的天朝自尊受到了极大的挫伤。正因为现实中的挫败感与失落感特别强,需要有一种心理的补偿,所以这一时期汉语音译外来人名的“汉化”倾向就特别明显。比方说,在二战之前与二战期间常常见诸中国报端的政治人物张伯伦,从中文看很容易让人觉得此人姓张名伯伦。尤其是“伯伦”二字,还透着浓浓的古典韵味,让人既生亲切感,又生崇敬感。实际上,此公并非中国人,而是地地道道的洋人,是年至年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ArthurNevilleChamberlain(—),汉语音译的全称是:亚瑟·内维尔·张伯伦。对照英文原文,我们知道“张伯伦”实际上是英文姓氏Chamberlain的音译,只是因为汉语音译时有意以三字音节呈现,首字又选用了百家姓中的“张”字,这样就暗合了中国人单姓复名的三音节命名模式,一个英国Chamberlain姓氏就被彻底地“汉化”成了一个中国姓名,融入汉语表达的报纸新闻中,就让人莫辨真相了。事实上,此“张伯伦”并非姓张名伯伦的汉人,而是“非我族类”的英国人。熟悉世界现代史者都知道,亚瑟·内维尔·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期间因为对当时的希特勒纳粹德国实行了“绥靖政策”,从而助长了德国法西斯势力的气焰,最终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个具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又比方说,丘吉尔和罗斯福,也是一看就像是汉语的两个人名,因为“丘”与“罗”都在百家姓之中。实际上,丘吉尔是二战时期的反法西斯英雄、英国首相WinstonLeonardSpencerChurchill(—),汉语音译的全称是: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罗斯福是美国第32任总统FranklinD.Roosevelt(—),也是二战时期世界 的反法西斯英雄、美国历史上 连任总统达四届的政治人物。丘吉尔和罗斯福二人姓氏的汉语音译,跟张伯伦姓氏的音译一样,实际上都是译者在汉人天朝自尊受到挫折而又难以消除“天朝心态”的潜意识的语言行为。反观汉唐时代中国强盛时期与今日中国国力鼎盛、开放自信情势下的汉语音译情形,就很不一样。当中国处于真正强势地位时,中国人的心态往往比较开放,并无排斥外来事物或外来文化的倾向。如汉唐时代中国对于外来事物以及外来文化(如佛教等)的包容态度,汉语对于外来词的包容态度,都可以看出中国人无明显“汉化”外来事物、外来文化的倾向。又如今天中国大陆对于外来事物、外来文化的空前包容态度,还有汉语对于外来词的广泛接纳度,都可以看出中国人开放、自信的心态,汉语吸收外来词过程中有意“汉化”外来词的倾向也因此明显少多了。如上面我们提到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还有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其人名音译不仅无明显的“汉化”色彩,而且还带有明显彰显其“非我族类”的性质。 尽管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越来越明显,今天我们有意“汉化”外国人名的情况不是太突出了,但是中国人潜意识中“以我为中心”的“天朝心态”是自古至今都客观存在的。“也许身为中国人(特别是汉民族人)早就潜移默化在文化血液之中,所以自己并不会意识到。但是,作为外国人特别是精通中国文化的西方汉学家,他们却对此看得非常清楚。正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所以为了求得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学术界的认同,他们常常为自己取一个中国名或是将自己的名字译得像中国名,其中又特别重视取一个在‘百家姓’中能找到的汉人姓氏。”[5]例如费正清、高本汉等名字便是如此。美国 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JohnKingFairbank的中文译名是“费正清”。“这个汉文姓名,是根据其英文名的谐音而译,不仅符合汉民族人取名的三字模式,而且有一个‘百家姓’中常见的‘费’姓。因此,不知其人,只闻其名者,一定以为这个‘费正清’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人。”[6]瑞典 汉学家、歌德堡大学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的中文译名“高本汉”也是音译,也特意挑了一个百家姓中的大姓“高”,名字“本汉”更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他“本是一个汉人”。“费正清与高本汉都是西方 学者,也是最精通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他们给自己取名或译名主动‘汉化’自己,正是缘于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对汉民族人的语言心理有着深刻洞察的结果。其实,费正清与高本汉主动‘汉化’自己姓名的修辞行为,并非孤立现象。现今正活跃于全球汉学界的许多汉学家,他们的取名或译名都有主动‘汉化’的倾向。”[7]高本汉的弟子马悦然也是这样。他是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本名GoranMalmqvist,他的中文名字可谓非常地道。“这个译名,无论是姓氏‘马’,还是名‘悦然’,都会让不知就里的中国人误认为他是一个汉人。”[8]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WolfgangKubin的中文名字是“顾彬”。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惊人的评论,人们经常在中国各大新闻媒体上见到其大名。“总之,不管是中国人给外国人音译名字时有意为之‘汉化’的修辞努力,还是外国汉学家主动‘汉化’其名,都清楚地说明了一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9] 三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灿烂的文明与文化,历史上一直处于人类文明的高端地位。因此,中国文化对于周边诸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外交流非常频繁,交流的历史也非常悠久,由此在中国古籍中留下了许多有关外国的地名(包括国名)。 众所周知,外国地名与人名一样,翻译时只能音译。从汉语音译史来看,早期汉语音译外来地名(包括国名),跟音译人名一样,主要追求“信”与“达”的修辞境界,即尽量摹写其地名(包括国名)的原始读音,选用读音上最接近其发音的汉字(即“信”),用字力戒成词有义,让人一见便知是外来地名(即“达”),而不是有意“汉化”其名,让人不觉其为外国的地名(即“雅”)。下面我们不妨先来看两个例子: (4)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 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甕。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篮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史记·大宛列传》) (5)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后汉书·西域传》) 例(4)是西汉时代司马迁记载张骞奉使出使大月氏回国后向汉武帝报告出使西域诸国所见所闻的话。其中,涉及了很多当时西域的地名(国名)。司马迁记录张骞所说的外国地名,皆采音译方式。“匈奴”、“康居”、“乌孙”、“扜罙”、“于窴”、“楼兰”、“姑师”、“月氏”、“奄蔡”、“安息”(即今之伊朗)、“条枝”(即今伊拉克)、“黎轩”(即古大秦国)、“篮市”、“身毒”(即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等,是全音译式;(大)宛”、“(大)月氏”、“(小)月氏”、“(大)夏”、“妫(水)”(即今阿姆河)、“弱(水)”,则是音译名加汉语词修饰或说明。但不管是哪一种,从选字对译来看似乎都看不出司马迁有明显的“汉化”外国地名的主观倾向。例(5)是南朝宋时范晔所记载西域地理的文字。其中,“身毒”在南朝时译成了“天竺”,“黎轩”译成了“(大)秦”,“月氏”仍承袭西汉时的译名,“高附”“磬起”则是南朝时新译的后汉时代的西域国名。除了“大秦”之外,其余的地名(国名)仍然是采全音译形式,仍然看不出有明显的“汉化”外来地名的迹象。 如果一定要追究《史记》《后汉书》中上述音译地名(国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也许“康居”、“安息”、“(大)夏”、“(大)秦”、“匈奴”、“身毒”、“天竺”等译名可能(也只能说是可能)反映了译者潜意识中的某种情感倾向。比方说,“康居”“安息”“天竺”等译名,选字组合后便有了一定的褒扬语义,反映出译者对其国家正面的情感态度。而“匈奴”“身毒”,选字音译时渗透了译者对其国家某种负面的认知与情感态度。因为历史上匈奴人一直是欺负汉人的,汉人对其有发自内心的仇恨,以“奴”名之乃是一种仇恨情绪的宣泄。印度河流域湿热多蛇蝎的环境,可能让中国古人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认为生存于其地的人也应该身体带毒,故有“身毒”的音译用字。“(大)夏”、“(大)秦”的译名,可能是比附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夏、秦二朝,以“大”字修饰足以反映译者的心态。当然,这些只是我们今天对古人音译心理的推测,并无可以佐证的依据。也许诸如“康居”、“安息”、“天竺”、“匈奴”、“身毒”、“(大)夏”、“(大)秦”等译名,当初只是音译者随意选字而成,并无什么微言大义,是客观的照音对译。关于这一点,也许我们从“印度”的译名历史可以略窥一二。古印度旧称“婆罗多”(因为一个叫“婆罗多”的国王曾一度统一了印度河流域,建立了国家),又称“身毒”“天竺”“信度”“忻都”。印度河中国古书上有译成“身毒河”的,也有译成“信度河”的。今天我们地理书上标记的印度河下游的“兴德省”、印度河与阿姆河之间的“兴都库什山脉”,其音译“兴德”“兴都”都是由梵文sindhu音译而来,跟司马迁《史记》所音译的“身毒”是一样的,只是用字不同。今天我们统一写成“印度”,乃是源于唐代。唐代高僧玄奘《大唐西域记》有曰:“译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归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印度。”意谓将梵文sindhu音译成“身毒”“贤豆”都不准确,正确的音译是“印度”。可见,中国古代至少在唐代时音译外来地名(包括国名)追求的还是“信”的修辞境界,即音译要准确地对应原文的发音,而无有意“汉化”外来地名的主观倾向。 如果说汉、唐两个最为强盛的王朝与最为衰落的南朝的译者尚无明显的“汉化”外来地名的意识的话,那么越到后来,随着中国王朝的更替和中国国运的盛衰,对于外来地名(包括国名)音译的“汉化”倾向就不能不说越来越明显了。比方说,柬埔寨是中国西南一个小国,中国古代对其国名的称呼有很多,在唐宋之前,有“究不是”(《后汉书》)、“真腊”(《隋书》《宋史》)、“吉蔑”、“阁蔑”(《新唐书》)、“真里富”(《宋史》)等译名。到了元代,则又有“占腊”“甘孛智”“澉浦只”等译名。元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总叙》有曰:“真腊国或称占腊,其国自称曰甘孛智。今圣朝按西番经名其国曰澉浦只,盖亦甘孛智之近音也。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到了明代,则又有“甘武者”(《明史》)、“柬埔寨”(万历以后)等。在这些对柬埔寨的音译名中,“甘孛智”“澉浦只”两个译名可谓在发音上最接近原文。那么,为什么在元朝时对柬埔寨的称谓还是“甘孛智”“澉浦只”,而到明朝时却转写成了“柬埔寨”呢?这恐怕跟元、明两朝中国人的心态不同有关。元朝是蒙古人统治中国,而明朝则是汉人重回执政,因此汉人“以我为中心”的天朝心态复萌,在外来地名(国名)音译中便有了“汉化”的修辞努力。 如果说在明代中国人音译外来地名(包括国名)时便已显露出“以我为中心”的天朝心态,显现出有意“汉化”外来地名(国名)的倾向的话,那么近代(鸦片战争之后)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了。众所周知,明朝是汉人执政,赶走了曾经横扫欧亚大陆、不可一世的蒙古人,自以为是一个强大的王朝。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天朝心态又死而复萌了,看待世界与周边国家的眼光不同了,因此在音译外来地名(包括国名)时“以我为中心”的天朝心态自然流露出来,音译出来的地名便打上了鲜明的“汉化”烙印。而到了近代,由于从年鸦片战争开始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挫败,中国从虚幻的“天下 ”的 跌落下来,中国人的天朝自尊受到了极大的 ,由原来的极度自尊变得极度自卑。然而,极度的自卑又往往产生极度的自尊、自大心理。表现在语言中,我们就见到了近代汉语的很多音译词都带有浓厚的“汉化”色彩。地名音译也不例外,这无疑是中国人潜意识中“以我为中心”的天朝心态不自觉的展露。比方说,美国加州有一个 的城市SanFrancisco,既是太平洋沿岸的 港口,同时也是华人在美聚居的重要城市,有 的唐人街,因而中国人到访美国必到此一游。SanFrancisco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甚至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因为它在中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旧金山”。其实,熟悉历史者皆知,SanFrancisco最初并不是城市,而是19世纪因淘金热而逐渐聚集了人气而成为城市的。早期的中国在美劳工为了生存,加入淘金者行列,多居住于此,所以称此为“金山”。后来,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也发现了金矿,成为新的淘金热中心,于是SanFrancisco遂由“金山”改称为“旧金山”。从英文原文看,无论是“金山”,还是“旧金山”,都不是美国城市SanFrancisco的音译名称。SanFrancisco真正的音译名称是“圣弗朗西斯科”,但是不论是当年在美的华工,还是近代诸如孙中山等往来于中美的政治活动家,都不称SanFrancisco为“圣弗朗西斯科”,而是节译SanFran而成“三藩市”。事实上,孙中山的著作与书信中也都是这样写的。SanFrancisco写成“圣弗朗西斯科”,其实是最贴近原文发音的,其音译可谓臻至了“信”的修辞境界。但是,事实上,中国人最愿意也最乐于接受的音译则是“三藩市”。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三藩市”的音译是经过了“汉化”处理,看起来听起来都更像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名,而且“藩”在汉语中是有特定含义的(中国历史上常称周边小国或附属国为“藩”),满足了中国人潜意识中“以我为中心”的天朝心态。对于身处异国他乡 层的中国人来说,这种阿Q式的自我满足,实在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心灵慰藉。虽然以“三藩市”对译SanFrancisco不是太贴近原文发音,在“信”的方面稍稍有所欠缺,但在达意传情方面效果却非常突出,可谓“达”“雅”兼顾。因此,从整体上看,“三藩市”的音译可谓臻至了外来地名音译“信达雅”修辞的完美境界。 又比方说,意大利中部有一个城市,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 的艺术中心,叫Firenze,现在的通译是“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及其译名,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了。但是,20世纪 十年代,这个意大利城市却有另一个非常文艺的译名“翡冷翠”。不仅译音非常接近意大利语,而且译名非常具有意境。因为它将“翡翠”的视觉与“冷”的触觉结合起来,贴合了这座城市给人的印象。据游历过这座城市的人说,这座城市的“官邸和教堂专用一种绿纹大理石,将城市点缀得如同一粒翡翠。(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asaoa.com/nsly/5622.html
- 上一篇文章: 26城淮安涟水国际机场最新时刻表来了
- 下一篇文章: 摸鱼达人非偶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