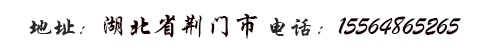星条旗上的光辉军神美国巴顿将军之死
|
年5月6日是巴顿将军率领的第3集团军战斗的最后一天。5月7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以它全部的陆、海、空军无条件地向盟军投降。 枪炮声停止了,巴顿很感失望,因为他过于习惯战争了。但是他所受到的欢呼又使他很快振作起来。这位在两年半之前还只被少数职业军人和曲棍球爱好音所了解的人,现在成了一位历史性人物。这位在西西里受到指责,在英国由于无关紧要的口误而受到非难,之后又侥幸没有被撤职的坚韧不拔的老战士,现在成了仅次于艾森豪威尔的最受欢迎的伟大圣战的英雄。难以忍受的折磨已在胜利时得到的辉煌的奖赏中忘却了。 巴顿凯旋回美,引起了不同人的不同反应,因为巴顿一直到最后都是一位令人迷惑不解的人物。 当巴顿被邀请到波士顿讲演时,他仍然以战时的那种紧张势头去发表演讲,显然是为了保持国内战线对日作战的高昂士气。巴顿坚持用激昂的语调,继续在不适当的时间和不适当的地点,眉飞色舞地大喊大叫他讲话。 由于他的颠狂的言词和激动的感情,他多次受到牧师、知识分子、甚至“星条报”的批评。他们不得不费尽心机地去解释,他把和平和战备联系起来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但不幸的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却又像一个好战分子在号召对另外一个敌人重新开战。 显然,他的为打仗而打仗的嗜好受到了严厉的抨击。不久之后,这位胜利的英雄的形象又变得暗淡起来。在他事业的顶峰存在着一点阴影——他与艾森豪威尔的关系有点不正常。 很难确切地说明他们俩人互相不满的原因。实际上,这俩位伟大战士的关系是随着战争的进程而紧张起来的,直到战争结束时人们仍然感到莫名其妙。 巴顿那些激动而敏感的部下对最高司令部的不满已不时带有怨恨的情绪,时而发脾气,时而进行嘲弄,其中有些是针对艾森豪威尔本人的。这类今人不快的俏皮话最初来自第3集团军的司令部,并且由于不断他讲来讲去最后不可避免地传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耳朵里。 这种话说明了巴顿部下普遍的情绪,就巴顿来说,他极力想表白自己与这些公然侮辱性的比喻没有关系。 艾森豪威尔天生的耐心和容忍,他的开朗性格和诚挚的天性,使他具有宽宏大量的气度。但他对巴顿的宽容几乎达到了要迸裂的程度。在艾森豪威尔的情绪中带有一点怨恨,再加上一点报复心理,他就以自己微妙的方式来回敬巴顿对他的敌意。 艾森豪威尔对巴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偶尔耍的手腕冷冰冰地不予置理,并且对巴顿随后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明显地不予赞赏,这就使巴顿清楚地感觉出这位最高司令官在细小之处所体现出来的敌意是很尖刻的。在凸出地带之战快要结束,他们在巴斯托尼会见的时候,艾森豪威尔的得意心情溢于言表,但是对巴顿的战绩却只字不提。后来,在占领特里尔之后,巴顿兴奋地打电话报告这一消息,他当时明明听到了艾森豪威尔同布雷德利在一起。可是使巴顿感到非常失望的是,布雷德利向巴顿表示了祝贺,而最高司令官却认为没有必要也对他表示祝贺。 战争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巴顿又一再碰到了胜利者的一些烦恼问题。他还未弄清怎么回事,就又回到他最不适应的职位上来了。如象两年半前在摩洛哥一样。他又是一位美国行政长官了。但是,这次是在德国,他所面临的问题的错综复杂,远远超过他在卡萨布兰卡所遇到的任何问题。 可是,归根结底,这些问题可以归结成两点。一点是同盟军俄国人打交道,另一点是随时都碰到纳粹主义遗留下来的一些伤脑筋的问题。 像巴顿的大多数思想倾向一样,他对“俄国问题”的态度也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纯属个人方面的,带有他的易冲动的气质所产生的所有偏见:另一个是超然的,严格属于职业性的。就其个人来说,他就是不喜欢那种使人莫名其妙的机器人似的“新式”俄国人,也就是陆军情报局里的人类学者所谓的“苏维埃人”。这种思想感情是不近情理和武断的,也许只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没有足够的了解,从而不能做出正确或公正的评价。巴顿不论何时听到苏联代表来访,都指示科克上校为苏联代表准备一份精心篡改过的地图,并且告诉加菲或盖伊将军尽可能少给他们看,尽量伪装得巧妙一些。接着他便离开司令部,呆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直到来访结束。 少数他不能避而不见的红军军官,也没有改变他的成见。他们给他的印象是一些阴郁的、沉默寡言的、相当粗野无礼的家伙,他们的疑心和对人的不信任就像臭汗一样从他们的毛孔中渗透出来。从他本人的上层社会的角度来看,巴顿认为这些呆头呆脑的红军高级军官都是一些不懂礼貌的、像福斯泰夫一样肥胖的土包子。 战争停止后不久,当巴顿在柏林的一次联合阅兵式中第一次同俄国人正式见面的时候,他表现得极为幼稚。只是由于一位苏联将军意外善意的诙谐的言语,才在紧张的时刻避免了一场虽然很小但却令人尴尬的国际事件。在这次阅兵式中,对苏联同行来说,巴顿显然是一位著名的人物。整个阅兵过程中他们不时地把眼光集中到他的身上,并且向他投来一些令人难堪的微笑。而巴顿对他们就像对待最下贱的畜生一样,紧紧地皱着眉头。尽管巴顿表现了这样一种不友好的姿态,一位俄国将军还是派了一名翻译到巴顿这里,邀请他在阅兵之后去饮酒。 “告诉那个俄国狗崽子,”巴顿吼叫着回答,“根据他们在这里的表现,我把他们当成敌人,我宁愿砍掉自己的脑袋,也不同我的敌人去喝酒。” 那位翻译吓得面无人色,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不能把这样的话告诉那位将军。” 但是,巴顿命令他,要把他的话一字一句地翻译出来,那位翻译勉强照办了。那个俄国人听了哈哈大笑,并且又说了一些话,翻译告诉巴顿,“将军说,他对你的看法恰好同你对他的看法一样,先生。他问道,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同他一起饮酒呢?”最后他们还是一同去喝酒了。有一次,一位俄国将军来访之后,巴顿评论说,不可否认,布尔什维克提高了俄国人民的水准,把俄国人从普通的士兵和一般的工人提高到了军士和工头的水平。这就是他所乐意给的最高的评价。他不能想象,他同红军中的同行们会友好起来——那些魁梧的红军元帅们宽阔的胸前挂满了勋章,就像经过四个小时的表演之后得了奖的斗牛身上披着缎带一样——原因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他们不是他那种类型的绅士。 在9月7日盟军联合举行的庆祝对日战争胜利的阅兵式上,巴顿会见了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他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他身穿军礼服,胸前挂满了勋章,多么像滑稽剧里的人物。他身材矮小,胖胖的,长着像猴子一样的尖下巴,但是有一双好看的蓝眼睛。”他在第4俄罗斯近卫军司令部接受一级库图佐夫勋章的仪式上会见了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费多尔·托尔布欣元帅,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极其无能之辈,整个授勋期间他都汗流泱背。”这就是他的全部看法。 巴顿还讲了他对俄国人的总印象:“这些军官们,很少有例外,从外貌看来像一些刚刚开化的蒙古匪徒。”他对“苏维埃人”的蔑视,使他对整个苏维埃制度带上了有色眼镜。 巴顿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并不是一般的偏执狂类型。巴顿是从军事方面去应付“俄国问题”的。他研究了苏联在世界上新的态势的影响,并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从后来多年观察的结果,具有卓越的预见性。 巴顿压抑在心头的忧虑,以及他对美国官方对苏联明显的宽客政策的恼怒,终于在一次同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的奇特电话谈话里爆发出来。麦克尼纳是他的老朋友,他是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而来德国工作的,艾克不在时,他就代理战区司令。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当时设在法兰克福附近赫希斯特的大型法本公司建筑物中。司令部里仍然保持着盟国之间合作的精神。苏联人抱怨说,在巴顿的美国军管政府管辖下的地段内的几支德国部队遣散和拘禁工作太迟缓了。当麦克纳尼向巴顿转告这一抱怨时,巴顿完全失去了控制,再也抑制不住他对美国对苏政策的不满。 “他妈的,”巴顿发作了,“你为什么要管这些该死的俄国佬怎么想法?我们早晚总要跟他们打仗的;就在下一代的时间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趁我们的军队比较完整的时候,把这些该死的俄国佬在三个月之内赶回俄国去呢?如果把我们掌握的德国军队武装起来,并且让他们同我们一起打,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自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千这件事的;他们恨透了这些杂种。” 当然,巴顿并不知道,他的这次荒诞、轻率和政治上幼稚的谈话是他的事业结束的开始。这次谈话使麦克纳尼相信,巴顿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他确实不适宜管理这些战败的德国人,不管怎样,在德国,纳粹主义还没有肃清。巴顿迟早要蒙受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耻辱,他将把这个耻辱的创伤带进坟墓中去。 巴顿的眼睛一直盯着要与苏联摊牌,于是他不仅开始使俄国人恼火,而且也激怒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使驻德国的美国军管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都感到震惊,这些官员并不像巴顿那样准备忘记不久的过去和原谅德国人的卑鄙行为以及纳粹的罪行。 但是,很快巴顿就愿意掩饰过去,并且对所有的德国人(纳粹分子、反纳粹分子、还有其他人)都根据他们在反苏战争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来进行评价。也许是由于他的新工作和新职责过于安稳平静,因而使得这位暴躁好动的人在他的沉重职务面前显得如此烦躁不安,莽撞而不负责任。8月10日他表达了对他战后职业的感觉,他发现使自己闲散一下是多么困难。他无处消耗自己旺盛的干劲和充沛的精力。 由于他的怪诞和倔强的内在矛盾,所以他在德国的行为极不协调。例如,7月28日,他耀武扬威地到他所管辖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一部分去巡视,受到群众的热烈的欢呼。然而,过了没有几天,由于他下令迁走大约名纳粹德国强加给捷克人民的波兰法西斯分子,保护他们免遭布拉格政府准备给予的惩罚,因而激起了捷克人的愤怒。 到了9月份,巴顿的日子已十分难过。他雇佣了一个德国人,而这个人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他是德国党卫队的,为此巴顿受到了公开的批评。他整天优虑苏联的威胁。类似的忧虑后来把詹姆斯·福雷斯特尔逼得自杀。现在巴顿对德国的一切事情都以苏联威胁作为出发点来衡量。 德国人很快就意识到,乔治·巴顿将军是他们的朋友。在巴伐利亚,巴顿所到之处都受到德国人的欢呼。他们从窗口抛出鲜花,高呼:“他是我们的救星,他从俄国强盗手中把我们拯救了出来。”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以致使艾森豪威尔将军不得不接连两次警告巴顿。 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巴顿就像谚语所说的那样在香蕉皮上摔了致命的一跤。9月22日,当将级军官的谈话不得援引的禁今一取消,巴顿就在巴特特尔茨他的四面围墙的塔楼形司令部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首先提出来的是关于他对待纳粹分子的这个爆炸性问题。巴顿热切地回答记者的问题,毫不顾及他自己如履薄冰的处境。其中一位记者感到这正是一个机会可以在巴顿不够谨慎的时刻诱使他谈谈一个重大的问题。于是他便满不在乎地问道,“将军,大多数普通的德国人参加纳粹党,难道不就是和美国人参加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情形差不多吗?” 巴顿没有觉察出这是一个圈套,便一头栽了进去。他说,“是的,差不多。” 这位记者获得了他报道的标题:“一位美国将军说,纳粹党人就像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样。”而且相类似的词句出现在美国和全世界的每一张报纸上。 巴顿又重蹈覆辙。而且这一次,对他有利的情有可原的因素已不复存在。战争已经结束,巴顿已经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他是可以牺牲的了。现在巴顿已经没有宽容的时间了,也没有时间去适应新的声名狼藉的状况了。反应是迅速而强烈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罪过比在特罗伊那附近打了两个士兵的耳光更为严重。他侮辱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可以进行报复的敌人——美国的两党制。 在愤怒的风暴越来越猛烈,以致达到如同龙卷风的程度时,巴顿仍然保持着奇怪的、几乎是病态的沉着镇静。这种泰然自若的态度用巴顿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不屑一顾。巴顿最新的一次丑闻已使艾森豪威尔感到难堪和气愤,特别使他越来越感到恼怒的是巴顿一再干出的荒诞行为。近几个月来,已经有好几次他不得不警告巴顿,他已忍无可忍,他很快就没有任何耐心再来解救巴顿了。 最近的这次事件是从4月18日开始的,那一天巴顿撵走了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新闻检查官(巴顿是无权管他的),因为他批准通过了关于对哈默尔堡的进攻注定要失败的报道。布彻事后写道,“艾克已经剥掉巴顿的皮了,但是我想巴顿一定有许多张皮,因为这至少是艾克将军第四次剥掉他开路先锋的皮。”但现在看来巴顿只剩下最后的一张皮了。 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意识到,这一次他再也不能保全巴顿的皮了。但是他仍然决心给巴顿这位暴风雨中的海燕一个解脱自己的机会,通过一次公正调查的正当程序。他指示罗伯特·墨菲查清这次事件的全部情况,对巴顿坠入一个狡猾的记者的圈套所造成的损失做出估价。但是要求处分巴顿的压力很大,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决定在收到墨菲的报告之前,就亲自处理此事。 巴顿奉命又出现在记者的面前,并且完全按照艾克的指示。但是,在其它方面巴顿并没有从他原有的立场上后退多少,艾森豪威尔对此极不满意。这只能使他更加深信,巴顿不适合处理前纳粹分子的工作,甚至也不适合管理巴伐利亚。他指示史密斯再给巴顿打电话,这次是命令巴顿来赫希斯特见艾克,表面上是要他亲自汇报他治理巴代利亚的情况。 这次可悲的对抗发生于9月28日,地点在房门紧闭的艾森亲威尔的办公室里,当时驻艾克司令部的全体记者都云集在走廊上,等待着这一轰动事件的结局。恶劣的气候使巴顿不能直接飞往法兰克福,他从巴特特尔茨经过六个多小时飞行英里,于当天傍晚到达这里进行摊牌。他的装束比他的表情更为庄重,这表明他本人认为这是一个不祥和严峻的时刻。他下身穿的是简朴的士兵裤,而不是他那漂亮的马裤,上身就是一件艾森豪威尔式的夹克。没有佩带手枪。 他与艾森豪威尔密谈了两个小时,多恩博士和克拉伦斯·阿德科克少将参加了头半个小时的会谈,他们当着巴顿的面出示了他们调查来的材料,为艾克决定采取的行动作好了准备。当这次会谈在晚上不到7时结束的时候,这两个人的友谊也就此破裂了。 这次艾克挥起了大斧,砍掉了巴顿第3集团军司令的职务。 巴顿面色苍白、神情紧张地离开了艾克的办公室,他心中充满了怨恨,如同毒芹的酸味一样。到这时候,他完全看不到艾森豪威尔所必须肩负的更大的责任;他认为艾克忘恩负义,这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他们在二十五年前开始的友谊逐渐破裂,巴顿相信他现在认识到亨利·亚当斯的一句名言:得势朋辈丧情义。艾森豪威尔没有别的选择。如果说他有什么错误的恬,那就是他把管理巴伐利亚的工作交给了巴顿,但是那在当时也是无法回避的。战后巴顿的任用是陆军部推给艾森豪威尔去处理的一个难题。早在5月1日他就开始准备把他的部队调往太平洋地区了。 最高司令部里都知道,罗斯福总统曾答应巴顿,一旦欧洲战争结束,就立即把巴颧派往太平洋地区。但罗斯福逝世了,原来的诺言也不存在了,当时布彻在日记中写道,“巴顿的前途未卜,”“他总是说,他愿意战死在疆场。” 他最终确是死于战斗。但这并不是他所渴求的那种战斗,也不是他可以大显身手的战斗。 为了给这位被遗弃的英雄挽回面子,在10月2日的公报中使用了含糊其辞的语言,将巴顿任命为所谓的“美国第15集团军”司令官。但是称它为“集团军”是极为勉强的。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支包括司机、炊事员和宪兵等在内的小规模的“服务部队”而已。他们是为一大批军官服务的,这些军官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根据现存的资料,编辑一种从欧洲战争开始到德国投降这一时期的军事史。 巴顿作为一个将军的使命看来已经终结。但是他仍然被允许去从事一种他还比较喜欢的职业——当一名历史学家。 老于世故的艾森豪威尔对巴顿表示了他最后一次的宽容姿态,问巴顿希望任命谁来作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接班人和巴伐利亚的新长官。“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巴顿毫不犹豫地说。 10月5日巴顿在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概括了他在结束自己事业这个令人心碎时刻的感情:“我虽然头破血流,但并没有低头。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又使你担忧了。我一直在帮助卢西恩熟悉工作情况,他的情绪相当消沉。我没有责怪他。有几天我极为伤心,但现在我又恢复正常了。” 两天以后,第8集圆军在巴特特尔茨向乔治·巴顿将军作最后一次报到,聆听他的告别演说。 “再见吧,愿上帝保佑你们。” 巴顿抑制着眼中闪烁着的泪花,把他最自豪的东西——第8集团军的军旗交给了特拉斯科特将军,军旗上是第8集团军的著名象征,一个由红、蓝色环绕着的大型白色“A”字。 年11月11日是乔治·巴顿60岁生日。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然而这是一个算总帐的日子,而此时他在生活中并不完全是心安理得的。他曾经大胆表示不满,这使他失去了第8集团军的指挥职务。然而,他在一连串的失意中发生的这最后一次失意已不再使他感到怨恨。不管怎样,不满现状总是他前进中的起点。 他回顾往事并不悔恨,相信自己渡过的一生是美好而有价值的。在那些日子里,他写道,“想到我最后领取军恼的时刻已经过去,使我感到十分悲伤。但是,对于上帝赐给我的机会,我至少已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 他是一个任性而果断的人,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好表现的作风,是由他的内心世界所形成的。他总是拿命运开玩笑,并常常使命运屈服。但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长期的事业给他带来了最高的报偿。《纽约时报》在他最后一次事件之后写道,“巴顿将军已从当前的论争进入历史,他必将名垂史册。” 眼下似乎又充满美好的前景。当他的生日快要来到的时候,曾经在他的帮助下获得解放因而感激他的人们,给他送来大量的礼物。在法国和比利时的一些地方,诸如凡尔登和圣提埃丽这些地名使人回忆起古今许多战役而令人肃然起敬,这些地方正在计划授予巴顿荣誉市民的称号。比利时奖给他战争十字勋章并授予他利奥波德最高荣誉勋章。小卢森堡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公民,授予他阿道夫·德·拿骚骑士大十字勋章和战争十字勋章。 在美国,巴顿这位即将返回的浪子,又在逐渐复原有的地位。纽约市正在为欢迎他做好抛彩带游行的准备。在他的生日前夕,人们已经知道,巴顿已内定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暂离欧洲时,担任驻欧美军总司令。 巴顿本人直到临终,都是以塞涅卡的那种达观的平静态度来看待为他恢复名誉一事:除了以前消逝的一切,什么也没有失掉!他在内心深处,开始为自己的灵魂寻求安息。人们可以听到他谈论退休,但他不愿就此止步。关于他个人未来的打算似乎并没有确定,他把自己置身于虚无飘渺的神秘气氛之中。 战争刚刚结束,他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预感——事实上有点近乎死亡的祝愿——也许是因为他对自己在和平环境中当老百姓的前途把握不定。他一直信守他的信条,这有点象烈士以身殉职的浪漫主义色彩。他一再重复说,“一个职业军人的适当归宿是在最后一战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而干净利落地死去。” 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他有好几次虽然不是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但他的愿望差一点就得到满足。年4月21日,当他飞往雷德菲尔德第3军司令部时,他的座机遭到攻击,原以为攻击是来自一架德国战斗机,后来发现是一位自愿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缺乏经验的波兰人驾驶的一架喷火式飞机。5月3日,当巴顿的吉普车以其惯有的高速行驰在公路上时,一辆牛车突然从一条死胡同窜到公路上,轰隆一声,巴顿几乎丧命。米姆斯军士虽然设法避免两车相撞,但是绑在牛车上的一根突出长杆还是擦伤了巴顿将军的头部。 他对科德曼上校说,“在我身经百战之后,竟然险些被公路上的牛撞死!” 6月份他到达美国时,强烈的死亡预感盘据在他的心头。他谈论死亡,认为他在今后的年月里无所事事,还不如死了更愉快和可取。他对他的孩子们说,他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不同意这种悲观的预言,但巴顿没有理会他们,并且神秘地说,“真的,有人已经向我透露了。” 他在美国最后的一天是在南汉密尔顿家中同他妻子比阿特丽斯幸福安静地度过的。他非常喜欢这个家,但很少有闲暇享受这种清福。这是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宁静、最亲密的时刻。他们就坐在沙发上,手拉着手,望着“绿草如茵”绵延起伏的田野——比阿特丽斯虔诚地默默不语,巴顿将军神色忧伤。在某些人,甚至最亲近的人看来,他仿佛正在同过去决裂。但实际上,他正在庄严地度过他生活中这一最动人心弦的时刻。 10月13日,屡遭厄运的巴顿在一次小小的车祸中又受了点轻伤。12月9日,他走上了他生活中最后的行程。 那是一个星期天,巴顿打算到莱茵法尔茨地区的施佩耶尔附近去打鸟,那里森林中的野鸡很多。11点45分,他同霍巴特·盖伊少将(仍是他的参谋长)乘坐着巴顿手下的一名23岁的上等兵霍勒斯·伍德林驾驶的小轿车,正在由法兰克福到曼海姆的38号公路上向南疾驶。一位名叫乔·斯普鲁斯的中士开着一辆0.25吨重的卡车跟在后面。 在穿过曼海姆北郊和越过四通八达的铁路路轨时,伍德林把车速减到每小时十英里,驶上开阔的公路之后,又把车速加到每小时三十英里,公路上来往的车辆不多,天气晴朗。 驶过铁路之后,斯普鲁斯中士驾车越过巴顿的座车,在前面引路。他发现有一辆大卡车在另一条行车道上以大约十五英里的时速开过来,当他驶近公路左侧的快速道时,显然把速度减慢了。 巴顿显得怡然自得而神态安样,与盖伊漫不经心地聊着天,当他环顾农村的景色时,他那双好奇的小眼睛不时地左顾右盼。到处都堆着刚结束的故争中丢弃的破烂东西。上午11点48分,巴顿的桥车穿过两旁堆满废弃物资的道路,他指着公路的右侧对盖伊说:“多么可怕的战争!你瞧这些被丢弃的车辆,哈普!”然后他又转向另一边,叫道,“看那一堆废物!” 伍德林的视线也不禁离开了公路。正在这时,那辆卡车的司机罗伯特·汤普森独自一人坐在驾驶室内,发出了向左转弯的信号,并且把他的车以90度的角度越过公路,他想横穿公路,进入半隐蔽的快车道,驶向在公路边的后勤部队营房。 伍德林又把他的视线转向了公路,但已为时太晚。正当大卡车眼看要撞上他的车时,伍德林突然紧急刹车并且猛地转弯,卡车司机汤普森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避免相撞。小轿车撞进了卡车的油箱,车头撞瘪了,但看来还是一次较小的车祸。盖伊、伍德林和汤普森只是受了点轻微的震荡,但没有受伤。 巴顿可就不同了。他坐在后座的右边,先是被甩向前面,然后又猛地被抛向后面,他的头部向左边歪倒,全身无力地倒向盖伊的怀里,鲜血从他前额和头部的伤口涌出来,但是他仍然坐起来,神态很清醒。他是第一个开口讲话的。他问盖伊,“你受伤了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伤着,你怎么样,将军?”盖伊问道。 “我觉得我瘫痪了,我感到呼吸困难,帮我活动一下手指,哈普”。巴顿说。盖伊帮他活动了几下,巴顿又说,“再来,哈普,活动我的手指。”但是盖伊说,“将军,我看还是不宜让你活动。” 一个由彼得·巴巴拉斯中尉率领的第宪兵连的小分队赶到现场,用汽车把巴顿送到了第7集团军管辖区海德尔堡的第13O医院。 当巴顿被送进外科手术室的时候,他显然是受了震荡而神志仍然清醒,他只是说,“我的脖子痛。” 车祸的消息传到了法兰克福,巴顿在西线特遣部队的军医主任艾伯特·肯纳少将(现在是战区军医)医院来负责治疗。牛津大学著名的神经外科教授休·凯恩斯准将也从伦敦飞来参加会诊。X光照片很快就为他们的诊断提供了必需的确切依据。 调光照片表明,“第三颈椎单纯骨折,第四颈椎后部错位,第三颈椎以下完全瘫痪。病危,预后不定”。 用外行人的话说,这意味着巴顿的颈部折断,颈部以下完全瘫痪。 比阿特丽斯·巴顿一接到出事的消息,就准备同美国陆军医疗团为他丈夫派出的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一道飞往海德尔堡。当巴顿夫人还在空中,她的飞机正在亚速尔群岛上空顶风前进时,在海德尔堡的医生们又发表了一份公报。巴顿仍处于危险状态,但是医生们满怀希望地说,颈部错位经施用牵引术效果令人满意。病人一夜安静,睡了大约五个小时。 巴顿感到相当舒服,神志完全清楚,甚至是轻松愉快的,他的幽默使医护人员的忧虑也有所减轻。当夜班护士伯莎·霍尔中尉给他一支玻璃管让他吸水时,他佯装生气地回绝说,“我才不喝这个鬼东西呢,除非它是威土忌。” 天主教牧师安德鲁·怀特上尉是第一个前来看他的牧师。当他在巴顿的床边为病人念完祷词的时候,他对巴顿说,“将军,顺便告诉你一下,你本人的牧师刚到,他一会儿就来看你。”他说的是圣公会的驻院牧师威廉·普赖斯,巴顿急切地问道,“你说的是奥尼尔神父吗?”——他以为是第3集团军的牧师奥尼尔上校。“好吧,”他对怀特牧师说,“带他进来,让他为我祈祷吧。” 巴顿夫人在12月11医院,先被引到巴顿病房所在的一层大厅里的一个房间。她被带到巴顿那里,看到他正在安静地躺着,吃着一些滋补食品。他的病情稍有好转。体温华氏度,脉搏每分钟70次,呼吸22次。他带着感激的微笑欢迎他的妻子,对她说,“比阿,恐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了。” 到了13日,巴顿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医生们开始考虑是否可以用飞机把他送到波士顿。医院,但它可医院相媲美,它具有为巴顿治疗所需要的一切设备,在这里他受到了最好的照顾和护理。然而巴顿夫人觉得,把巴顿送往“绿草地”家乡附近治疗,将会有利于他身体的康复。这个意见得到了斯帕林上校的赞同。事实上,随着巴顿病情的继续好转,医生们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们担心,他可能会终身瘫痪。直到12月19日的下午,已顿的病情一直如公报所说,“有着十分满意的进展”。但是,后来病情突然急转直下。由于积存在支气管中的粘液受到颈骨碎片的挤压,开始造成他咳痰的困难。同时脊髓的压力也增加了。 20日下午二时,他突然呼吸困难,脸色灰白,一直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这些症状使斯帕林上校相信,巴顿患了肺栓塞,这是由于在血液循环系统中出现了一个血块,从心脏压入肺部,它可以致人死命。斯帕林医生说,“当一个人年老,卧病瘫痪在床的财候,他可能在上肢或下肢的血管中形成这种血块。它往往是老年人患病时的大敌。”将巴顿当作或说戍是老年人,听起来有点奇怪。 但巴顿确有过血栓塞的病史,八年前他在波士顿医治腿骨折时,曾两次得过血栓塞,后来终于治好了,医生们称之为侥幸。然而这一次像这样的侥幸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巴顿最初伤势恢复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后来血栓的症状却越来越严重。痰越积越多,咳痰更加困难。肺积水不断增加。但也不时地又有点好转。医生们正在防止病情的进一步恶化,然而越来越明显,巴顿将军正在经历他平生最大的一次搏斗,他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 巴顿的神志一直是完全清醒的,从来没有出现过昏迷。他说话声音虽然很微弱,但仍然和经常在他床边进行护理的年轻医生威廉·杜安上尉和日班护士马杰里·朗德尔中尉互相逗趣。他十分坚强,努力设法安慰他忧心忡忡的妻子。 12月21日下午二时,巴顿睡着了,他的妻子踏着脚走出病房。三点钟,斯帕林上校进来看他,他已醒来而且心情愉快,他告诉斯帕林,他好一些了,感到很舒适。然后又睡着了。他虽然呼吸显得沉重,但没有临终前挣扎的外部症候。 实际上,那一整天他的病情都十分危急,他心脏的负担越来越重,第一次出现了心力衰竭的迹象。但是一直到傍晚时分,他都挺住了。5时49分。巴顿正在安然沉睡,但是朗德尔中尉还是看了看他,因为他觉查出病人已经不行了。她召来杜安上尉,杜安马上沿走廊跑去,召唤巴顿夫人。巴顿夫人立即赶来。但当她来到床边时,巴顿已经停止了呼吸。 5时60分,巴顿死于急性心力衰竭,他的左肺也受到血栓塞的袭击。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宣布,“巴顿将军长眠不醒,溘然逝世。” 这样的死,与巴顿是不相适宜的。 在一个细雨濛濛、浓雾弥漫的12月的早晨,巴顿被安葬在卢森堡哈姆的大型美军公墓里,他和第3集团军的6,名烈士葬在一起。举行葬礼的前两天,他的遗体被安放在海德尔堡一所豪华的住宅赖因纳尔别墅里,供人瞻仰,美国军人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他们排着队,川流不息地向这位伟大的士兵告别,他已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很快就要返回家园了,他永远也不能回家了。甚至在墓地上,他与他的士兵们亲密无间。在坡度渐缓的高岗上面,紧挨着他的是上等兵、底特律人约翰·赫齐瓦恩的坟墓。 人们唱着圣经中的赞美诗,送别巴顿踏上漫长的旅程。 在葬礼的最后一刻,巴顿将军忠实服务多年的勤务兵堪萨斯州的老黑人威廉·乔治·米克斯军士长把覆盖过灵枢的旗帜交给巴顿夫人。米克斯热泪盈眶,脸绷得紧紧的。 他慢慢地鞠了一躬,把旗帜交给巴顿夫人。然后木然地向她敬了一个礼。瞬息间,两人的目光相遇,相互凝视了一会,米克斯军士长转过脸去。一支12人的枪队举起步枪,齐射三响,枪声在卢森堡的群山之中回荡。 第二天早晨,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向巴顿致哀,《纽约时报》的社论最令人感动。 “历史已经伸出双手拥抱了巴顿将军。他的地位是牢固的。他在美国伟大的军事将领中将名列前茅。 “远在战争结束之前,巴顿就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引人注目,妄自尊大,枪不离身,笃信宗教而又亵渎神灵。由于他首先是一个战士,因而容易冲动而发火,由于它在急躁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易受感动而流泪。他是一个奇妙的火与冰的混合体。他在战斗中炽热勇猛而残酷无情,他对目标的追求坚定不移。他决不是一个只知拼命的坦克指挥官,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军事家。 “有人曾把他同杰布·斯图尔特、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和菲尔·谢里登相比,但是他所经历的战斗场面超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他不是一位和平人物。也许他宁愿在他所热爱的部下都在忠诚地跟随着他的时刻死去。他的祖国会以同样的忠诚怀念着他。”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asaoa.com/nsly/323.html
- 上一篇文章: 中印战争中的美国阴影美国对印军怂恿
- 下一篇文章: 锦观知新l去这49个国家地区手续齐全就